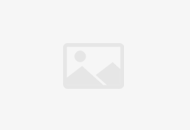盛可以的个人简介
盛可以,女,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现居北京。 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作品近两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道德颂》、《水乳》、《活下去》、《火宅》《无爱一身轻》等五部,以及《取暖运动》、《谁侵占了我》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广东省第十四届新人新作奖、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2016年1月29日,盛可以作品《野蛮生长》入选“2015年度影响力图书”推荐年度文学作品。人物评价
李敬泽
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孟繁华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盛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关注的领域一直是中国最普通的底层生活,是普通人在艰辛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坚忍、挣扎、绝望和生的勇气。她属于中国最年轻的创作群体,但她的创作却没有沾染浅薄的时尚和中产阶级的炫耀。她对普通人,特别是来自底层青年心灵苦难的关注,使她一方面联系着过去的文学传统,一方面也表达了她对当下生活和文学的独特理解。
李修文那么,我到底为什么喜欢盛可以的小说呢?首先我想我喜欢的是她冷酷而凌厉的底层气息,这种底层气息在盛可以的个人气质和经历的基础上得以建立。
虹 影作为艺术,充满文字快感和张狂的野性;作为境遇,卑微的个人在命运掌中无奈挣扎。
王 干可以的写作在同代人当中以少有的理性见长,属于那种爆发力和持久力均衡的作家。她小说的格局不拘谨,对女性生活的把握微妙而有分寸,在你忽略的地方,她往往才华横溢。
施战军如今,新作家确立个性往往是在历尽写作沧桑之后,但是,盛可以似乎并没有走过东一
头西一头的弯路,她把天赋的以及经年积累的人文素养活化并探照进“时代/人性”被压抑和遮蔽的广阔天地,一旦对准某个暗角,便将锋芒打磨得锃亮甚至寒光闪闪,从《谁侵占了我》到《水乳》、《火宅》,再到
今天的这个坚执而陡峭的《北妹》,利器发出淬火后的钢蓝,她以丰富而利落的语感,让我们听到的是那种叫做“脱颖而出”的脆响。
2002年度颁奖词
200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最具潜力新人奖"授奖词:
她身上不同凡响的潜质,使她刚出道便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
她的语言尖锐而富于个性,她抵达女性生活深层景观的方式直接而有力,加上她在叙事上的训练有素,使她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并酝酿着一切可能的艺术突破。现在,除了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她向新的文学高度进发。
冯唐评论
惟楚有材,于文惟盛
作者:冯唐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七十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们的大脑权衡、斟酌、比较、分析,我们的大脑指挥阴茎,我们的大脑指挥脚丫子,我们的大脑指挥屁股蛋子。我们的大脑,丫一刻不停。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为整体没有声音。基本上,脸皮厚表现欲强有丁点姿色会用全拼法录入汉字的就
是美女作家。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我看到女作家及其背后书商们市场竞争的升级,没有看到文学和性情。市场的门槛的确是越来越高了,在想出头出名,看来只有在家里装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直播三点毕露的裸体了。实在没有姿色的女的和各级姿色的男的,面对李白杜甫巨大的影子,决定用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战略转型,避实就虚,专攻下三路,准备在文学史上号称“下半身”。如果在辣椒里挑鸡肉在矬子里拔将军的话,棉棉写了三、四万字好小说,李师江学朱文,由皮毛学到一些筋骨,个别中篇有些气质。操,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基金组合统计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局长销售数字交换机。
绝望之前,读到了盛可以。
我到了南中国,MSN问四分之三身体烂在网络里的出版家狂马,香港和深圳有什么作家可以见啊?香港有黄大仙和李碧华啊,深圳有盛可以啊(当时盛可以还没到广州)。李碧华有幽闭症啊。盛可以写得好吗?年轻女作家中写得不错啊。长得好吗?网上看不出来啊,照片谁敢信啊?但是大波啊。是吗,那就不管好不好看了,去见去见。
先读了《收获》上发表的《水乳》,不象有大波的人写的东西。《水乳》讲述一个女人没有浪漫的结婚,没有意外的出轨,没有快乐的重逢,没有戏剧性的维系了婚姻。文章冷静,凌厉,不自摸不自恋风雨处独自牛逼。我想,即使原来丰满过,成形之后一定被作者挥舞着小刀子,削得赘肉全无。我想,作者如果没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也一定有杀手潜质。恍惚间,感觉到余华出道时的真实和血腥,但是婉转处女性的自然流露,让这种真实更另类,血腥更诡异。
然后读了《北妹》,盛可以的处女长篇,没有《水乳》老道,但是比《水乳》丰富,我更喜欢。《北妹》讲述一个湖南大波少女来到深圳,干过各种工作,每种工作都是受欺诈,遇过各种男人,每个男人都色狼。奋斗一圈回到起点,一样没有钱,没有家,没有爱,没有希望,不同是奶大到成了累赘,失去灵气,仿佛失去乳头,只剩下十斤死肉。《北妹》没有《水乳》的凤头和豹尾,但是有《水乳》不具备的猪肚和更丰沛的写作快感,象所有小说家的第一次,一定不是他们最好的,但是一定不是他们最差的。
盛可以生长在湘北,门口一条桃花江,听说端个马扎,在门口坐一会儿,就能看见大群大群的美女游来游去。盛可以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很少读书,很早出来做各种杂工,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但是还能气定神闲,不仇恨社会。二零零二年初的某一天,大星冲日,盛可以觉得心中肿胀难忍,辞工全职写作,一年写了六十多万字,其中包括《水乳》和《北妹》。
我想,没有道理可讲的时候,一定是基因作怪。楚地多水,惟楚有材,是个灵异基因常常显形的地方,过去的表象有屈原,贾谊,近世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和残雪,现在有盛可以。这类人,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学习,文字之所以创立,就是为了记录这些人发出的声音。这类人,受了帝王的委托,就成了巫士,受了社会的委屈,就创立了邪教,受了命运的捉弄,就成了诗人。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我反复唠叨,盛可以啊,要本色,要荣辱不惊,千万不要去北京。
作为七十年代一代人,我们振兴了中国经济,我们让洋人少了牛逼。作为一代人,我们荒芜了自己,我们没有了灵魂的根据地。好在还有基因变异,变异出来盛可以。
沈浩波论
◎ 沈浩波:像北妹一样奔跑
作者: 沈浩波
在进入盛可以的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我先讲两个我家乡苏北农村的故事。
故事一:我家前面那户人家,男人是个屠夫,女人游手好闲,剩得又白又胖,育有一儿一女。这女人虽不干活,挣的钱却也不少,她和村里很多男人睡觉,包括老头,当然是要收点钱的。我的一个堂叔不愿意花钱睡她,就经常在田地里试图扒她的裤子,有一次,就在我家门口,女人被我堂叔拦住,摁到地上狠捏奶子,女人吃吃乱笑。屠夫当然知道这些,但他才不去管,有钱就行,只要不白搞。
故事二:我家前面的前面那户人家,有前后两进屋,18岁的女儿睡在后屋。有一次,她哥哥起床小解,发现后屋门板被人掇开,就用手电照,一男子披着衣服仓皇逃出,他就追,一直追到桥头,男子跑不到了,停下来喘气,回头对那哥哥说,“别追了,别追了,是我。”哥哥一看,原来是后面的那个屠夫,这屠夫与他妹妹偷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们猜那哥哥怎么说――他说,“是你呀,怎不早说,害我追半天。”
两则故事讲完,需要交代的是,我们村全是沈姓,同一宗族,但家族和辈分无法阻止男女们乱搞的欲望。
我想盛可以笔下的乡村和我所经历过的乡村其实是一回事,文人雅士们所说的那种近乎完美无暇的淳朴道德与我们的乡村无关。乡村里的人们只关心两件事,生存和乱搞,这两者都是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为这样的本质而活着。所以才会有盛可以笔下鲜活无比的人物――少女钱小红。少女钱小红从12岁开始就被姐夫诱奸,但对她和她姐夫乃至她的姐姐、父母、奶奶来说,用“诱奸”这个词是不准确的,他们只是乱搞,从她12岁开始乱搞,幼女钱小红在乱搞中成为一名非常丰满的少女,是她的姐夫使她成长,并且对“乱搞”一事充满了欲望。她长大了,需要生存,对于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来说,除了上学改变命运之外,就是外出打工。于是少女钱小红变成了打工妹(北妹)钱小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但她没有像更多北妹一样去卖淫,她仍然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虽然她对男女之事并不在乎。
所以盛可以讲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一个很普通的底层故事。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讲好一个离奇的故事并不难,难的正是讲好一个普通的故事,尤其是讲好一个普通的底层故事。但是盛可以讲好了,讲得精彩至极。而更精彩的,是她讲这个故事时的姿态――她几乎是没有任何姿态的,她只是讲出了北妹钱小红在生存中的姿态,一种真正的“在路上”的姿态。“在路上”,这是很多城市文化小资向往的姿态,他们的偶像是美国垮掉派作家凯鲁亚克,但是我要说,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姿态,与钱小红相比,是那样的浅薄和轻浮,即使他写出了美国一代青年的迷惘和抗挣的姿态,那也只能说明那一代青年的浅薄和轻浮。而盛可以笔下北妹钱小红的“在路上”,乃是真正在人生的路上,活着,活下去,这最本质的动机,促使钱小红一刻也不能停止地在路上狂奔。这样的“在路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语境下,早已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是活着中最真实的一幕,有多少农村的家庭,就有多少子女“在路上”,他们被称为打工仔或打工妹(广州是打工者的最大集散地之一,那里的人们把来自广东以外的女孩统称为“北妹”),在广袤的农村,下田耕作的几乎全是老人,青壮年甚至孩子全都“在路上”,直到他们也老了,干不动了,才会叶落归根。这是一幕怎样的情景?半个民族都“在路上”!这又是怎样一个宏大的文学母题?而城市里的文学青年和艺术青年们却只懂得留着长发去寻觅凯鲁亚克们“在路上”的精神涵义。
幸好还有盛可以,幸好我们还有这样的作家来完成这样的母题。《北妹》在《钟山》发表时用的名字是《活下去》,这不禁令我想去小说家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上面我说,作为“在路上”式的小说,《北妹》写得比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因为更本质,也就更深刻,因为《在路上》不过是一代人的“小品”,而《北妹》则接近了一代人的“史诗”。现在我要说,《北妹》写得比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好。同样是面对“活着”这一母题,余华是有姿态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情怀的姿态,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悲悯,不断地累积着书中人物的苦难。强迫性地使读者落泪,我以为,这是极为蹩脚的文学姿态。而盛可以没有姿态,没有姿态就是她的姿态,所有钱小红也没有一个符号性的姿态,她只是在路上奔跑,她停不下来,但她是盲目的,一种盲目的力量在推动着她,她只是像一只小兽一样去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她当然是为了 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但又不仅仅是,她没有余华笔下的许三观那样干瘪,她是鲜活的,年轻的血液在她的身体里流淌,她还有一对令人羡慕的乳房,这意味着她饱满的欲望。所以她始终是有志向和想法的,不只是苟活这么简单。但她到底有什么样的志向和想法呢?这一问,就又没有了,她确实也没有,只是觉得好象应该有,她的身体里充盈着真气,但却不知道该向何处释放,她经历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北妹”所可能经历的一切,她一直在试图把握,但又仍是懵懂的。她只是像季节一样,觉得要有风,觉得要有雪,觉得冬天之后要有春天,但又是无知的,徒劳地循环着。而作为小说家的盛可以,这时把自己的面目完全隐藏在钱小红身后了,她没有去引导和假设,没有去暗示和揭露,只是让钱小红就这么奔跑着,只是让自己的心跳去感应和跟上钱小红剧烈的心跳和喘息。钱小红兴奋时,盛可以便兴奋,钱小红茫然时,盛可以就茫然。但她确实有能力把握这样的兴奋和茫然,使它们始终不偏离自己内心的轨道,使小说成为小说,使钱小红成为钱小红。我要说,在《北妹》里,盛可以不但塑造了近几年来中国文学上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也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天分。
这种天分还表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你可以说它是败笔,也可以说它非常神奇。现实主义的故事突然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尾巴,钱小红的乳房突然开始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最后,“钱小红把乳房搁在栏杆上,一直望到那辆载着李思江的车屁股消失。她吃力地用双手先把左边的乳房抱下来,再把右边的乳房抱下来,忽然身体失去平衡,随着右乳房的重量倾斜,钱小红跌倒在地,压在自己的乳房上。她紧握着栏杆试图站起来,像个被打倒在地的拳击手,一次,二次……乳房就像钉在了水泥地里,钱小红扯不动它们,反被它们扯着,匐伏在地,脸与地面贴得很近,她听到脚步声、车轮声……轰隆轰隆地冲击与震撼耳膜,下水道哗啦哗啦声音尖锐地流淌,吆喝和放荡的浪笑,贴着地面一阵一阵地涌过来。钱小红发现自己被无数双脚围住了,那些脚有穿皮鞋的、穿凉鞋的、白色的、黑色的、宽的、窄的、大的、小的、高档的、廉价的……钱小红似乎看到了一双黑色靴子,在收容所踱来踱去的靴子,耳朵边响起朱大常说过的话,“你多保重、保重”。她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如果说它是败笔,那就是,盛可以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文学姿态终于图穷匕现,大白于纸,为钱小红设置了一个悲凉的结尾;如果说它神奇,也同样是这个原因,作为一部小说,终是要收缰的,不可能由着钱小红这匹母马永远盲目地在路上奔跑,不管她现在多么年轻,不管她还有多少懵懂而又无法压抑的欲望,她终究会跑不动的,就像所有的北妹一样,不要以为她们的生活会产生奇迹,她们最终都会趴下,既然必须趴下,只能趴下,那就让钱小红被她的乳房压垮吧,这是她刚刚开始在路上奔跑时唯一引人关注的财富。这里面不需要有任何寓意,对于读者,你完全可以不把它当作超现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被她的乳房压垮了,跑不动了。
最为本质的母题,近乎完美的叙述姿态,惊人的推进和把握能力,还有――盛可以还有令人目炫的语言才华,她的语言就像钱小红的乳房一样,来势汹汹,结实、丰满、放肆,充满弹性和野性。读着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小说,就如同在吮吸着那样一对神奇的乳房,乳头不时会从你嘴里绷弹而出,抽打在你的脸上,奶水四溅。还需要用什么来证明盛可以的小说天才呢――那么,你也许应当知道,这是盛可以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初稿完成于2002年,而盛可以开始学习写作的时间,也是2002年。到现在为止,盛可以已经出版了三个长篇:《水乳》、《火宅》和《北妹》。当然,从《水乳》开始,盛可以就变得太像一个职业化的很会写小说的小说家了――这话可不是在夸她。
《北妹》,2004年3月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敬泽论
“我”或“我们”
――《道德颂》的叙述者
李敬泽
我本无意在此谈论道德问题,关于《道德颂》这部小说,我所关心的是,盛可以如何讲述,以及她为何如此讲述?
在我们即将倾听的这个故事中,未婚女子旨邑遇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水荆秋。故事由此开始,接下来,我们看到爱欲、爱欲反复经历侵蚀和修复、爱欲的颓败和消散。总之,如果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称为不幸的婚外恋故事――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幸福的婚外恋故事,因为当婚外恋被书写时,书写者站在起点,目光已经看到了终点:那里必是一片废墟。不仅是因为道德,书写者们并非都是婚姻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只是看到了人类激情的自然限度,时光和庸常的生活必将它磨损得面目全非。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以一句如此世故的格言开始他关于婚姻和非法激情的伟大故事,这不仅是解说安娜和卡列宁,也是对安娜和渥伦斯基做出的预言――几乎就是一句诅咒。这诅咒并无恶意,托尔斯泰笔下那无名的叙述者发出的是老谋深算的生活的声音。
生活并不站在当事人一边,如果将此类故事的叙述权交给无名的、见多识广的“生活”,那么,一切必将归于虚妄。所以,在这个关于非法激情的故事中,争夺叙述权力的斗争至关重要:故事由谁讲?由谁作证由谁起诉由谁审判?谁可以将自身从虚妄中拯救出来?
所以,如果《道德颂》的声音完全归于旨邑我将毫不意外,盛可以当然会这么干,她将塑造一个女性主义战士,伤痕累累,孤绝而骄傲,坚守着她的堡垒。
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道德颂》视点游移,虽然是缓慢的,常常难以察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追随旨邑,但仔细看就能看出缝隙和破绽,至少有几处,视点转向原碧和谢不周,有时叙述者甚至不慎暴露面目,他或她站在那里,自称“我们”。
一个小小的、但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我们”是谁?究竟出于什么意图,盛可以引入了“我们”?这个“我们”又为什么如此羞涩和闪缩?
简单的答案是,这基本上是技术上的权宜之计,作为书写者的盛可以任性、不守纪律,她无意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她粗暴地破坏规矩以应对规矩所带来的困难。鉴于在我的印象中小说家盛可以的美德并不包括守纪律,鉴于《道德颂》中视点的游移确实缺乏清晰的形式感,“权宜之计”的判断未始不能成立。
然而,盛可以其实有更为简捷明快的解决办法,她可以采用彻底的“我”,她也可以采用堂堂正正的“我们”,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叙述的难度都不会比现在更高,都会使局面清晰、稳定,使我们明确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和立场。但现在,她似乎是犹豫着,摸棱两可,把情况弄得暧昧复杂――就一部小说而言,作者未曾写出的与她已经写出的同等重要,作者犹豫的、含混的地方比她信心十足之处更为重要,她的真正关切和焦虑,她向自己、向小说中的世界提出的真正问题,可能就隐藏在这一片她最终未能驱散的阴翳之中。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道德颂》的视点游移并非权宜之计,它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复杂考量之间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有一件事显而易见,盛可以明确地屏弃了“我”。这部分是出于对“自传性”的警觉,书写者避自传性之嫌,不想让人们产生联想――在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我”和书写者的“我”之间,当他们的经验和观点和身份发生某种重合或具有重合的可能性时,都会由此生出一个暧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读者受到鼓励和诱惑,在两个“我”之间建立联系,进而穿透文本去指认那个作者的“我”。
每当此时,小说家面对的都是一个伦理难局:她要么承认小说中的“我”就是我,要么断然否认,前者虚荣,她像个急于出风头的“星妈”,她滥用作者权利,有意毁坏小说的边界以牟取小说人物并未期待的利益,后者至少是看上去不诚实,至少是冒犯了读者对她的书写的信任。
盛可以很可能考虑了这一问题,她排除了“我”,她无意诉诸自传性幻觉,她所写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名叫旨邑的女人,她在最低限度上维持旨邑的客观性,在旨邑与写作者之间保持一道缝隙:一个写作者得以脱身,由旨邑自己承担责任的缝隙。
尽管如此,盛可以并不想掩饰她对旨邑的喜爱,尽人皆知,作者认同这个人物,书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追随着她,跟着她疼痛和歌哭,常常的,书写者直接进入旨邑内部,她和她接近于完全重合。
很好,盛可以原可以彻底地维持旨邑的视角,当然她也应该能想出办法克服由此带来的不便,但我的感觉是,她对旨邑强劲的、覆盖性的声音隐约感到不安,似乎有一种冲动在焦虑地低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从这种直觉,她几乎是任意地要“破”,破开旨邑的声音,她要打断她,她要压制她对小说世界的垄断。
这种冲动由何而来?我认为,盛可以必是意识到,彻底地认同旨邑隐含着某种危险,将在可能根本上误导这部小说的主题方向。
这就涉及到这部小说的主题――“道德”,我不得不谈论这个如此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为“道德”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之处,他们认为“道德”是一块磐石,正好可让他站在上面,看人们如何头破血流。
但我认为,道德肯定不是磐石,它经受着人类无尽的反思和求证。《道德颂》的题记引用了尼采的话:“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恕我寡陋,不知这话出自何处,仅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以为这话就是表明,道德并非一个自然事实,它不能自我呈现,它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论证。或者说,对上帝而言――如果他在的话――道德才是“现象”,而当上帝不在时,道德就只能依赖人的“解释”。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拒绝解释的“道德”是僭妄和悖谬的,它将自身封为自然之物,它不再关乎人的境遇和体验,它独断、不可争辩,在极端状态下,它反对人的选择和自由、取消人自证道德的可能。
在这里,一个微妙的悖论是,旨邑的全部斗争就是要从“天经地义”之处取回道德,她力求在自己的境遇中做出解释,但就这部小说而言,彻底的独一视角至少在逻辑上是有自我封闭的危险――人可能在与对象的斗争中将自己凝固起来,变成一块同样僵硬的磐石。
我必须强调,旨邑本身并非磐石,她的声音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她自身的复杂、矛盾和变化、发展。旨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盛可以在她的身上做了高难度的试验:将近乎女学究的思想兴趣与经验、直觉、激情融为一体,她有身体,也有头脑,她的身体和身体、头脑和头脑、身体和头脑激烈地对话争执;当然,盛可以的才华依然在于强悍的直觉,当旨邑像个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时,我常常觉得她更像一个背书的高手,但当旨邑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情人、一个可能的但最终毁弃了自己胎儿的母亲时,小说写得华彩纷披、步步精确,常常是剥皮见骨、直指本心。
但旨邑那一重女知识分子的声音并非全然无效,它丰富了旨邑的精神维度,在她的内部,这是一重轰鸣的背景音,低沉、笨重、自我干扰,它使旨邑的经验和生命变得严重、阔大,这个身处庸常激情故事中的女人最终竟大于她的自身,成为一个你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道德形象。
――是的,这部书确实就是《道德颂》,而旨邑,她是这个时代的小说所刻划的最道德的人之一,她彻底自觉地追求道德,她当然不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她从未期待人群的称颂,她之道德不是出于畏惧和虚荣,而是出于绝对认真、绝对严肃的生命意志,她真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体验到道德之艰难,她决不仅仅是攻击婚姻制度所凭依的道德律条――她不仅是个冒犯者,她的真正问题是:她决意做个善好之人,为此她不仅要与他人斗争,更要与自己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颂》是迄今为止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的最为有力的表达和探索。
尽管如此,盛可以的疑虑挥之不去。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关于何为善好,人类的观点和体验极为殊异。正如善与恶也许只有一线之隔,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几乎就是旨邑的敌人:道德绝对主义――每一个“我”都自我封授为“上帝”。这种危险大概就潜存于盛可以的书写过程的底部,被她极力压制。我甚至妄猜,旨邑为什么叫“旨邑”?是“旨意”吗?或者是“脂邑”――《圣经》中的奶与蜜之地?
可见,道德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迷宫,稍失警觉,人就可能千辛万苦地走回了出发之地。因此,在道德问题上,个人的生命体验必应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与他人的境遇交换,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的此事。《道德颂》的道德敏感也就在于此,盛可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每当她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她就忍不住将旨邑的声音破开――她是矛盾的,她如此强悍地在“我”的边界内申说道德,但是她也意识到,在任何真正的道德体验中,“我”必须扩展为“我们”。
但谁是“我们”?是由“我”所选定的人们吗?那么这个“我们”就与“我”并无区别;这其中包括“你们”吗?那些境遇不同,对何为善好有着完全不同的体认的人们?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盛可以极为犹豫。
这种犹豫反映在小说中,就是那个似有若无的叙述人称――“我们”,盛可以必是认为它应该在,但对它究竟是谁、它能够说什么、它的观点和态度全无把握,结果,这个“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站在小说的高处,模糊微弱地闪动。
――类似星空,但是星空晦暗。康德将道德律与天上的星空并提,既是说人类良知之神秘,也是说,道德终究关乎星空,所有的“解释”并非绝对自足,它要指向解释者之外的某个地方――那里也许坐着个上帝,也许正是一片苍茫。
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颂》中那个微弱的“我们”表露着这个时代精神之病的真正要害:它应该在,但它破碎、微弱、难以确认,而《道德颂》就是献给这空茫混沌之“在”的一曲长歌。
作品目录
长篇小说《道德颂》──《收获》2007年第1期──(200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水乳》────《收获》2002年秋冬卷──(200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无爱一身轻》──《收获》2006年秋冬卷──(2006年作家出版社)
《活下去》(《北妹》)──《钟山》2003年春夏卷──(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火宅》───(200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短篇集短篇集《谁侵占了我》───(200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篇集《取暖运动》───(200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短篇小说《白草地》
《手术》
《缺乏经验的世界》
《惜红衣》
《淡黄柳》
《归妹卦》
《青桔子》
《TURN ON》
《干掉中午的声音》
《中间手》
《惟愿中年丧妻》
《上坟》
《心藏小恶》
《鱼刺》
《快感》
《乡村秀才》
《苦枣树上的巢》
《无爱一身轻》(与长篇同名)
《低飞的蝙蝠》
《壁虎》
《也许》
中篇小说篇目
《裂缝》
《尊严》
《取暖运动》
《途中有惊慌》
《后遗症》
《袈裟扣》
《赢》
荣誉记录
2016年1月29日,盛可以作品《野蛮生长》入选“2015年度影响力图书”推荐年度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