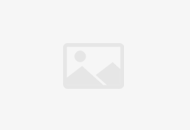桑原骘藏的个人简介
桑原骘藏くわばらじつぞう骘zhi,第四声日本人,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代表学者。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先后任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京都帝国大学。长期致力于东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桑原骘藏的生平
桑原骘藏(1871~1931),1871 年1月27 日出生于日本福井县敦贺,他的父亲名为桑原久兵卫,经营着一家和纸店。桑原骘藏是家中次子。桑原骘藏是家中次子,兄长名为桑原制一郎,弟弟为桑原贽三郎。
桑原骘藏的小学和中学在京都府立中学度过,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有名的京都第三高中。高中毕业之后,桑原骘藏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汉学科,并且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学院(日文中的汉字“大学院”即中国的“研究生院”),师从那珂通世,专门研究东洋史。桑原骘藏擅长英语和法语,因此选择了在当时尚属冷门的东西交通史作为其主要研究范围。
1898 年,桑原骘藏毕业,就职于东京第三高中,教授东洋史课程。同年,他自己在研究生期间开始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中等东洋史》完成并出版。1899 年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07年4 月,桑原骘藏前往中国,开始为期两年的官费留学和研究。在这期间,他游历了陕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东部等地。桑原骘藏在途中以日记形式作了详细的考察报告邮寄给当时的文部省,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分别以《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即《山东河南游记》)《东蒙古旅行报告》(即《东蒙古纪行》)为题连载。这些考察报告在桑原骘藏逝世之后由森鹿三等弟子进行整理,加上桑原骘藏游历期间的另外两篇短文《观耕台》和《寄自南京》,1942年由弘文堂书房出版,即《考史游记》。
1909年,桑原骘藏结束了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就任刚成立不久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东洋史第二讲座教授,负责东西交通史和风俗史的教学与研究。桑原骘藏用与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人不同的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待东洋史,并凭借他在东西交通史和风俗史方面的研究在京都帝国大学站住了脚跟。当时内藤湖南担任第一讲座教授,因而桑原和内藤几乎成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的代名词。
1910 年,桑原骘藏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后桑原一直在京都大学工作,直到1930年退休。1926 年,桑原骘藏因其《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通常简称《蒲寿庚考》)而获得日本学士院奖。
1931 年5 月24日,桑原骘藏因肺病在京都塔之段町的家中去世,享年61 岁。
(以上根据刘正《京都学派》、张明杰译《考史游记》译者序相关内容整理。)
桑原骘藏的主要学术成就与著作
桑原骘藏生前与死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等东洋史(二卷本)》《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东洋文明史论丛》《支那法制史论丛》《考史游记》等书。1968年,日本的岩波书店将这些著作集结,出版了六卷本的《桑原骘藏全集》。该全集的第六卷为别册,内容包括桑原骘藏本人所藏图书的目录和全集一至五卷的总索引两个部分,而桑原骘藏本人的著作为前五卷。钱婉约博士在其翻译的《东洋史说苑》的附录《〈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一文中提及《桑原骘藏全集》全五卷,这种说法可能专指前五卷专著,忽略了第六卷别卷。但严格地说,这种说法有误,《桑原骘藏全集》全六卷才为正确的提法。
在桑原骘藏著作之中,在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最广为人称道的应为《中等东洋史》和《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
《中等东洋史》作于桑原骘藏研究生期间,1898年首次出版。尽管成书时间比较早,但这并不影响《中等东洋史》在东洋史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作用和地位。桑原骘藏的以西方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东洋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治学特点在《中等东洋史》多有体现。在桑原骘藏的笔下,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是孤立于其他历史事件之外,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这些普遍联系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种或民族、区域形势等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将一个地区看做整体,或者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整体从而进行研究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但是从当时的角度来说,桑原骘藏的这种大眼光的确是有超前与进步之处的。《中等东洋史》已一经出版,就在当时的东洋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学校纷纷以此书作为东洋史学科的教材,中国的上海东文学社也在1899年引进了此书,由樊炳清翻译,王国维作序,以《东洋史要》为题出版。这也是桑原骘藏第一部被中国学者接触并接受的著作。在这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了几种《中等东洋史》的译本,成为了清朝末年颇受欢迎的中国史读本。梁启超评价:“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 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 "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黄现[对《东洋史要》评道:“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己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 傅斯年在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指出:“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由这些学界名贤对此书的议论,可知当时《东洋史要》在中国的影响。
《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则是桑原骘藏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内的重要著作。该文最初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杂志》上连载(1915~1918),后由岩波书店以《蒲寿庚之事迹》为题出版。1929年,冯攸将该书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以《唐宋元时期中西通商史》为题出版。同年,陈菁亦将该书译为中文并补充考证,由中华书局以《蒲寿庚考》为题出版(下文通称《蒲寿庚考》)。《蒲寿庚考》书分五部分:第一章,蕃汉通商大势;第二章,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第三章,蒲寿庚之先世;第四章.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第五章,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骘藏在考证蒲寿庚的个人事迹的同时,也深入地研究了唐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海上交流。桑原骘藏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史料,也收集了可观的西方学者的成果,这种丰富翔实的考证正是《蒲寿庚考》的特色。陈菁在他的译者序中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征引详富,道人之所未道。于中西交通之往事,发明不少,非徒事襞绩旧说者可比,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
桑原骘藏中国观
正如桑原骘藏本人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代表,桑原骘藏本人的中国观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而理解桑原骘藏的中国观,尤其是其中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批评与否定,则必须要首先了解桑原骘藏所处时代对他的影响。
桑原骘藏之前的近代日本中国观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军舰威逼日本开国,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随着锁国政策的结束,在西方的商品、技术、科技传入日本的同时,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史观也传入了日本。1887年东京大学史学科成立,聘请师承兰克的德国史学家里斯讲授和传播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当时的井坪九马三、重野安绎、白鸟库吉等教授,都是引进和实践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传入让日本的史学家开始接触到“科学的历史学”。
除了兰克实证主义史学以外,西方学者的史观,尤其是中国史观在日本的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停滞论”,这种观点源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否定。在这个观点中,中国文明基本被描述成一个停滞、落后、愚昧的文明。这种观点传入日本,使原来的崇尚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日本学者中的一部分开始通过另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甚至于中国历史决裂。
福泽谕吉是这类学者的代表,他的“脱亚论”更被认为是“遥承u2018中国文明停滞论u2019,是近代日本蔑视中国、批判中国观念的始作俑者”。在福泽谕吉的眼中,日本是正在朝欧美等文明国家的方向发展的半开化国家,而中国和朝鲜则是正在向非洲国家等野蛮文明退化的半开化国家。福泽谕吉认为,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日朝三国同为黄种人,同是东亚国家,同样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三者之间并无很大差距(东洋连带论),西方国家对待中朝两国的态度与评价,也就是对待日本的态度与评价。他认为,这一点会严重阻碍日本谋求在开国之后的新时代中的利益,因此日本若要发展图强,则必须要与中朝这两个“恶友”划清界限,并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这也就是福泽谕吉在其《脱亚论》一文中主要表达的观点。为支持这一观点,福泽谕吉从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因此,《脱亚论》就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界与中朝的绝交书。更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不仅与日本明治以来的领土扩张、发展国力、谋求日本的国际地位等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对后世的学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桑原骘藏的中国学桑原骘藏任教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被认为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但无论是从治学方法方面,还是从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态度方面,桑原骘藏与当时的京都学派学者们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治学方法上,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人秉承的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桑原骘藏对此多有非议,认为乾嘉考据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他从德国兰克学派那里学习并接受了兰克实证主义史学。但无论乾嘉考据学还是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两者都没有超出考证的范畴。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普遍具有比较深厚的考证功夫,这也算是他们的一大共同之处。
如果说在治学方法上桑原骘藏和京都学派的其他学者是局部差异总体一直,那么在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态度这个层面上则是正好相反。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大多都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比如狩野直喜对敦煌文书和宋元喜剧保持这长久的兴趣,并写作了大量的汉诗;内藤湖南从小学习《四书》和入学;小川琢治的父亲则是儒学教师。此外,这些学者们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反观桑原骘藏,则是及其排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他眼中,这些不过是一些能够用来引发一系列评论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反面教材,中国的学者在他看来是“脑子很糟糕”,因而他极少与中国学者来往。甚至于对于自己的研究,桑原骘藏也有诸如“我自己从事的是东洋史研究,和支那学没有任何关系”之类的言论。
以上的这些差异,就决定了桑原骘藏不同于其他京都学派学者的特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与否定。
《东洋史说苑》是桑原骘藏从自己的论文中挑选出比较通俗的23篇论文整理出版的,全书分7大主题:实事、文化、宗教、习俗、气质、人物、杂纂。其中,习俗篇中的《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支那人食人肉的习俗》《支那的宦官》,气质篇中的《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支那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等数篇文章非常直观地表现了桑原骘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蔑视与否定,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最能体现桑原骘藏的中国观。
对于中国人来说,桑原骘藏的批评的确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决不能因此就全盘肯定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蔑视与否定。
《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支那人辫のs史)》一文中,桑原骘藏先后阐释了金统治下的汉人辫发历史、元统治下的汉人辫发历史以及清统治下的汉人辫发历史。文章中叙述的汉人对辫发的态度如下:1、(明末清初)汉人虽然对女真人很顺从,但是一旦被要求剃发辫发,便会发起抗争叛乱。2、辫发的实行可能是因为朝廷的强制推行,也有可能是汉人的“迎合主义”。3、汉人在辫发实行之初对辫发怀有强烈的抵触,但是没有多久就习惯、接受并有一套完整的辫发习惯。桑原骘藏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人(汉人)在危急时刻的确会反抗,但一旦一件事情成为了既成事实,就会变得逆来顺受,迎合统治者。另外他还将明末的反清斗争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于汉人对辫发、易服的反抗情绪,并将南明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好好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
文章的第一句“中华民国が成立してから殆ど一周年”可以说明这篇文章大概作于1913年左右。从这个时间来看,桑原骘藏必然熟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必然对晚清政府的腐朽多有了解。19世纪晚期,正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正式确立与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日本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观点,譬如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确立起到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远山茂树认为《脱亚论》在走向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的路途中,也起着启蒙的作用;而石田一良认为,为日本对外扩张“在思想上进行辨护的是脱亚论”。正因如此,要说桑原骘藏完全不受外部影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于文章中关于中国人的“迎合主义”和逆来顺受,与其说是从中国历史中总结而来的结论,倒不如说是对腐败的晚清政府的真实写照。
《支那人食人肉的习俗(支那人食人肉の风习)》一文由俄国官员逮捕一名因粮食匮乏而在市场上贩卖人肉的中国人一事入手,例举了上自商纣王下至元末动乱时期的各类食人肉的例子,给出了食人肉的五大类型(1、凶年荒年,粮食不足;2、战乱导致粮食匮乏;3、有嗜食人肉的癖好;4、食极其憎恶之人之肉;5、因治病而以人肉作药引),并结合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说明食人肉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风俗。桑原骘藏本人在几年之后又关于这个问题,收集了更为详尽的资料,复作《支那人中的食人肉的习俗(支那人间に於ける食人肉の风习)》一文。
首先,且不说食人肉的事例几乎在各国的历史中都有所见,单说所谓的“食人肉的习俗(食人肉の风习)”的提法恐怕就有点言过其实。无论是日文中的“风习”还是中文里的“习俗”“风俗”,都指的是一种在社会常态下的百姓的行为,这既是说,一种行为一旦成为“风习”“习俗”“风俗”,便会被认为是一种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正常且合理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的存在具有普遍性。那么反观桑原骘藏所提出的五种食人肉的类型,尽管不同,但都有一个特点,即都是非常态的情况。凶年、战乱是对于国家来说的非常态情况,癖好、食仇人的肉、治病所需等是对于个人来说的非常态情况。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些非常态的情况都不会成为主流,因而只能说“食人肉”是一个在特定时期才会出现的非常态行为,而不是“风习”“习俗”“风俗”。
其次,桑原骘藏在这篇文章中的逻辑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例子,证明“食人肉”这一行为的存在,却没有深入分析“食人肉”为何会产生,产生的必然条件是什么。“食人肉”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但是能否因其存在就认为这种行为在中国被“几千年间持续不断地维持着”,恐怕这不是简单地罗列例子就能得出的结论。
再次,对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桑原骘藏在文中指出“为了很好地认识中国人,必须从表里两方面来观察他们。通过经传诗文了解中国人的长处优点固然重要,同时,对于其反面也必须认识领会。”而“很好地认识中国人”的目的则是为“图日中亲善”。但是从文章的行文来看,我们看的只是对“食人肉”这一非常态行为的夸大描述,这种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刻意丑化实在难以与“日中亲善”产生关系,与近代日本盛行的蔑视、敌视中国人的潮流倒是非常地符合。
以上只是浅析了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中的两篇文章,但他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所体现的中国观也已经能够管窥一二。
因为生活在特殊的时代,桑原骘藏的中国观是带有偏见的中国观,在他的中国观中我们能看到他在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下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样也能看到他受福泽谕吉等人影响对中国、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蔑视与敌视。因此对于桑原骘藏及其著作,必须严格地分别对待,不能因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就无视他对中国的偏见。
对于桑原骘藏的出生日期,目前有1870年12月7日和1871年1月27日两种说法。根据刘正在其所著《京都学派》中的考证与分析,笔者认为桑原骘藏的出生年月应为1871年1月27日。详细请参看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第63~65页。
]桑原骘藏著,张明杰译:《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译者序:《桑原骘藏和他的〈考史游记〉》
桑原骘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8页。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转引自《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桑原骘藏著,陈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译者序。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3月版,第214页。
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78页。
关于《东洋史说苑》所收录论文篇数,钱婉约博士在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一书中提到是23篇,而《京都学派》一书作者刘正却在书中写到《东洋史说苑》共24篇。但是岩波书店1968年出版的《桑原骘藏全集》第一卷《东洋史说苑》的“辨言九则”第一则明确指出,《东洋史说苑》是收录了桑原骘藏本人论文中比较通俗的23篇而成的,因此《东洋史说苑》一书所收录的论文篇数当是23篇无疑。
另外,在被收入《桑原骘藏全集》出版之后,《东洋史说苑》(即第一卷)实际收录的论文篇数却多达45篇,这与“辨言九则”中所提的23篇出入甚大,不知是否是由疏忽所,有待考证。
转引自周颂伦:《〈脱亚论〉再思考》,《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
桑原骘藏著,钱婉约、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中华书局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