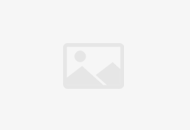沈作的个人简介
[约公元一一四七年前后在世](文献通考作仲矗┳置髟叮旁⑸剑萑恕I淠昃幌辏妓胃咦谏苄酥星昂笤谑馈I苄四杲俊4疚跫洌宰蠓钜槔晌麂钏靖晒佟R蚴桎钏旱厘霰慧溃崛佟2坏弥疽宰洹基本资料
姓名:沈作
性别:男
出生年月:不详
国籍:中国
时代:宋朝
籍贯:湖州德清县
民族:汉族
身份:官员
个人简介
沈作矗置髟叮院旁⑸剑莸虑逑兀裾憬虑逑兀┤恕
秦桧党人沈该之侄。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
绍兴十一年(1141年),任岳飞幕僚。岳飞罢官后,任江右漕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作《哀扇工》诗反映民间疾苦,掇怒洪州知州魏道弼(魏良臣),劾之,降三官。
在政期间对百姓照顾有加,减少他们的劳役,深受当地老百姓们的尊敬。
后曾出使金朝。著有《寓简》。
人物作品
哀扇工歌
某州竹扇名字著,织扇供官困追捕。
使君开府未浃旬,欲戴纶巾挥白羽。
新模巧制旋剪裁,百中无一中程度。
犀革镌柄出虫鱼,麝煤熏纸生烟雾。
蕺山老姥羞翰墨,汉宫佳人掩纨素。
衙内白取知何名,帐下雄拿不知数。
供输不办楚频,一朝赴水将谁诉。
使君崇重了不闻,呜呼何以慰黎庶。
闻道园家卖菜翁,又说江头打鱼户。
号令亟下须所无,官不与钱期限遽。
归来痛哭辞妻儿,宿昔投缳挂枯树。
一双婉婉良家子,吏兵夺取名为顾。
弟兄号叫邻里惊,两家吞声丧其妪。
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群空号呼。
杀人纵欲势位尊,贪残无道天所怒。
邦人蓄愤不敢言,君其拊马章台路。
新安采樵行
种粟上山椒,种禾水没腰。
田家作苦不如樵,炊桂之地甚不遥。
一艘千束莫复朝,顺风顺水不动桡。
归来醉饱吹短箫,野花插鬓樵女娇。
农夫忍饥自芸苗,粟米自熟腹自枵。
明年卖田卖山去,谁能辛苦输王赋。
【出处】:
中华诗词-全宋诗-沈作矗
沈姓起源
作为一个姓氏,“沈”也有好几种不同的来源,其主要分别就在读音之不同――有的人姓“审”音之沈,有的人则姓“真”音之沈,不可随随便便地混为一谈。
读“审”音的沈姓,是黄帝的后代。《姓纂》上说:“周文王第十子晡季食采于沈,因氏焉。今汝南、平舆、沈亭,即沈子国也。”
读“真”音的沈,即是颛顼帝的后代。《姓氏考略》上说:“《左传》沈姒蓐黄注,四国,台骀之后,系出金天氏。又,楚有沈尹氏,沈诸梁,并公族,以封于沈鹿得姓,则系芈姓,非一族,直深切者,为实沈之后,与音审者不同。”
由此可见,天下姓沈的人,有的是黄帝的后代,有的则是颛顼帝的后代,不过几千年繁衍下来,出自黄帝的那一支日渐人多族繁,于是大家也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求甚解”,一概的统姓起“审”来了。
根据上面所提的《姓纂》的记载,“审”音沈姓的人,得姓于周文王的第十个儿子晡季,也跟许多其他古老的姓氏一样,是因地得姓。当时的沈国,大致是现在河南省汝南县东南,以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一带地方。据《左传》的记载:“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据近世考据,沈亭的遗址,就在今阜阳县西北沈丘堡的东方,可见得“沈”姓真是一个有根有据的古姓。
至于“真”音沈姓最初发源的楚地,则大致是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一带地方。
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姓,历来倒未曾发现过被外族冒用的纪录。相反的,到了五代时期,却有分支为他姓的纪录――尤姓是从沈姓分出来的。
相关资料
《寓简》抄 宋?沈作 撰
●卷一
君人者居极否之世,能约己以厚下,则否倾而为益矣。居交泰之时,或剥下以封上,则泰过而为损矣。在《易》之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损乎?虽益也(震下巽上),损下而益上,斯为否矣。虽损也(兑下艮上),损上而益下,斯为泰矣。盖天下治忽之理不远也,戒在损益而已矣。
诚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于事物,陷于迷途,是以蔽而不自见。能复其自然之性,则昭然着矣。故《易》之《复》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诚之至也。
数始于一而终于五,天以藏德运化,妙其所以为数之始终,而神其所以为用之消长者,故虚一与五,退藏于密秘而弗用,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
“帝乙归妹”者,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阴慝也。此前人之说,可取。
“元亨利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备是四德,以统天而行四时,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随、临、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贞”者,不得与乾比也。盖屯以“勿利有攸往”、随以“无咎”、临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继“元亨利贞”之下,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临之《彖》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当,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贞”而已矣。
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皆屏绝,质之于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u2018得意忘象,得象忘言。u2019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谓元城固为学《易》者说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数固无用也,况讲解乎?
《易》之六爻,数用九六。先儒皆以谓九,老阳也;六,老阴也。君子欲抑阴而进阳,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阴阳,天道也,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其说皆不通。盖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数也。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夫参天,则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两地,则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义也。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为予言如此。
《易》者,至神之数,吉凶之先兆,使人见机而作,避祸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盖重《易》而系之者也。其于《易》之数,知之远矣,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而任其所谓在物者,则夫《易》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无蹈患害,果何预哉?冥顽嚣凶,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富贵没身者又何哉?圣人已矣,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穷《易》之道,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说也。
《易》之为书,虽不可为典要,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虽穷万物之变,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数之要,神妙不测者,圣人盖难言之也。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渺茫不见涯诶,广著图象,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以为自得之学,致使俗儒妄讥,竞为艰深之说。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自开辟以来,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邵尧夫非不知数,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勿论也。夫五物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其来久矣,不可阙一也。今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岂不生于土乎?如用邵说,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又可乎?盖自汉京房、焦贡之学流于驳杂,而扬雄又以四为数,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笃志之士,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说以叛正经。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于心,岂肯形之于说?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昔释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师。或问常何所得,常曰:“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耳。”道一闻而肯之。夫士之本无所得,又无所守,而随世谬悠,有不愧于法常者乎?
阴阳之气专,则生化之理灭。故至阳之中必有阴,而至阴之中必有阳,至其极则相生。离为火,而中画阴也;坎为水,而中画阳也。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卦终于《未济》,何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而道亦无尽也,若以《既济》而终,则万法断灭,天人之道泯矣。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浮屠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者,是也。
《易》者,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乐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
●卷二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犹可疑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可也;发而中节,谓之中可也。和顺积中,何喜怒哀乐之有?有感而应焉,无过不及也,则谓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谓知言。
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高。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己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其为《春秋》之说,谓“三《传》犹狱词,三《礼》犹律令,而《春秋》则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师省其词,审听其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之于法,吾无庸私焉。吾于《春秋》,求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书名之曰《春秋谳》,则其义也。
孔子谓兵可去,以至于食可去,而无信不立,虽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无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颜氏子不改其乐,世固莫能知之。予处穷困饥寒迫切,无可奈何,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而已。虽欲改其乐,又奚以为哉?将愁苦慨叹而忧之耶?忧无益于贫也,不若勿忧之为愈也。颜氏子则既闻道矣,予非知道者,直无可奈何而已!
孟子谓居移气,养移体者,是殆为常人言之。若豪杰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潜心,草庐高卧,气未尝屈也。岂以宫居为哉?采薇首阳,茹芝商山,体未尝病也。岂以食养为哉?后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说者,当自孟子发之。惜哉!
庄子之学贵清净无竞,然魏武侯欲偃兵,庄子乃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学贵智慧慈爱,然陆亘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师乃曰:“斯民涂炭矣。”孰谓佛老之教专尚虚无而远于治道哉?
●卷三
晋人雅尚玄远,宜于世情澹薄。今观其书尺,感叹睽离,极于凄怅沉思,缠绵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之语。所谓玄远淡泊者,得无妄乎?大率晋人以心迹不相关为自解免,此最是其膏盲也。
●卷四
韩退之谓高闲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其为心泊乎无所起,其于世澹乎无所嗜。予谓果能尔,则是颜氏子也,而何关于佛乎?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止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与我设?”子沈子曰:“子厚之学,谓天人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乱善恶无所主,灭祥为不足畏也。是使有国者逆天而慢神,为恶而弗知惧也。日月星辰之行悖于上,山川崩竭于下,阴阳之气谬戾于其间,而曰吾弗预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气而然耳,治乱非所感也:是贼夫君者也。
《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夫仕宦惟泽加于民乃为得志耳,故富贵得志为难。位卿相、禄万钟而志不得行焉,则亦何乐乎富且贵矣。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无所往而不遂者,惟隐居为可耳。
柳子厚作楚词,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
●卷五
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以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宜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犹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盖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难校,氵典涩而少工,词多陈熟,理无适莫。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其论作赋之工如此,非过也。
范文正公微时,尝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进显贵,入为执政大臣,出为大帅,其谋谟经画,所活多矣。于医则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观东晋殷浩妙解脉法,尝有给使叩头祈死,诘问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岁,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诊视,便有生理,退就屠戮无恨。”浩为按脉,处方一剂,便愈。于是悉焚经方。呜呼!浩功名大缪,幸有绝艺可以起死,而深讳其事,反以能活人为惭悔。自范公视之,浩可谓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强为其不能,宜其败也。
程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不学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东坡讥骂靳侮,略无假借。人或过之,不知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堕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过也哉?刘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
●卷六
今之学者谓得科名为了当,而仕宦者谓至从官为结裹。嗟乎!学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将以行志及民也。以浅俗不根之学声律对偶传习时文,一得科名,则已了当,一生而进德修业更无余事矣。以贪鄙无能之质巧佞卑污积累官簿,一得从官,则已结裹,终身而爱君忧国无余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时可哉?予见士大夫无贤愚其言皆如此,心窃怪之,而不敢辟也。又干求举状云:“得文字一纸二纸,可为之羞缩。”
人臣修身植德以俟天命,穷达得丧付之于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兴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责命于天而归过于数,故人主而至于言命之地,则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虽得君,要须使人主尊敬而惮,不可狎也。故言听谏行而不敢忽,汲长孺之于汉武帝,魏郑公之于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亲近而易之,则其言亦轻矣。宫之奇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已为敌国所料矣。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晓然明了,则应之;必易发之,必当不复加思虑而缓急皆中节矣。心之见未明也,物至则中挠而外变矣。凡处大事皆当易(难易之易)之。易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难;惟无心于成败祸福,而惟道之从、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强求其必成,亦不果于邀福也。列御寇曰:“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其知言哉!
《传》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谓上无邪僻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议其非,是也。而后世之监谤讳人开口论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议论政事,非庶人之职也。非职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家多偏爱者衰,国多嬖幸者危。人主自聪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乱而多制者,其政益纰。官聚敛而多费者,其积益亏;兵民穷瘁而怀怨者,其心必离。贤士失职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杀、上下刻急而无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乱亡,盖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天地阴阳之气无不与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类应。江海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木善升降以润万物,德泽之象也。王者之国必依山川。夏将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绝;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国都也。晋永嘉初,河洛江汉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泽不浃,水土无所演,国家空弱,民间膏血祜腊,灾异叠见,川原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盖难以类言也。
凡草木华实茎叶,一发生之后,归于枯朽,皆不能复生。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颗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万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强名之曰仁。呜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当之哉?
予壮岁尝于坐右书云:“侈心生当念败德,淫心生当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摄心以其所畏也;犹贤乎放肆不能自反者尔。又曰:“仰则求之于天,俯则求之于身,远则求之于古人,近则求之于吾君。”于天、于身、于古人者,无求而不得也,所谓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则有命焉。外是吾无所求矣。
一涉世俗,虽荣华富贵中,无一切如意事。比之贱贫违情,境界犹轻。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间,违物离人而立于独耳。仲尼谓隐居以求其志,圣言远矣。
君子当知命知时。时不可为,虽公师之位立谈可致,君子去之,谓命也。况命又不偶,其可强进耶?天下之事,成败天也,吾人也当与天争胜乎?
每闭阁焚香,静对古人;凝神著书,澄怀观道;或引接名胜,剧谈妙理;或觞咏自娱,一斗径醉;或储思静睡,心与天游。当是之时,须谢遗万虑,勿令相干,虽明日有大荣大辱大祸大福,皆当置之一处,无令一眼睫许坏人佳思。习熟既久,静胜益常,群动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穷通付之有命,万缘成败处以无心。
处困之极,时命未通,但可安贫守静,修心养气,以道自娱,一切外事,尽当屏绝。虽博戏谐谑、过从游观,亦且暂置。非惟省事,聊远悔吝。宴坐一室,数息宁神,隐忍无为,必逢亨会。有外事来触此境界,便当猛省,极力止之。
一生之计,通塞贵贱,自有定命;一家之计,饥寒饱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为也。营营何益,徒自苦耳。况世路方艰,惟退藏为得策。且只一觞一咏,笑傲自适,闭阁焚香,读书以穷性命之理,著书以寓经济之意,赋诗以发喜怒哀乐之心,浩歌以畅幽闲旷远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营营然者,力务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卷七
一气之运行,出入于身中,凡一时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一昼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气行无间,绵绵若存,寂然不动,与道同体。
视身如云,视世如尘,中有至真,其乐日新。
因闲坐有所得云:随顺空缘,等于觉观。
古语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予虽不事口腹,然每饭必有鱼肉蔬茹杂进,食气为五味所胜,盖未尝知饭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贫甚,久雨遂至绝粮。晨兴饥甚,念得饭足矣,不愿求鱼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杂他物谷实,甘香甚美,八珍何以过?欣然自笑。盖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饭之正味。其余不知者盖多矣。
古人谓事顺成而计工曰天诱其衷,谓事大谬而谋拙曰天夺其魄;然则一切得丧无非天也。计谋之工拙,天实使之;所谓人为者,特偶然耳。虽在人事,不得不尽,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为也。
诸器世间,惟无形者有大力,物莫能胜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虚实,故山河大地不能胜水,水之力不能胜火,火之力不能胜风。风居四之下,独为无形,而负荷地、水、火,终古不坏,大矣哉!以其虚而无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处善乐,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俭居身,以敬待物,以诚谨畏,自重毋过其分,此所谓常德正道,动则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则凶险危道,动辄致灾,居之不可安者。吾当择焉。富贵亦于是,贫贱亦于是,至哉安乎!
天下之患莫大于农失业、士失职、国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势也。
必有忍,其乃有济。功名以隐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胜,学佛者以无生法忍成道。忍,固难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马懿所谓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难也。
《灵枢经》言自然妙用以宝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诚。二者相为用而一也。圣人以无为体,以有为机。能入无为而应有为,能用有为而返无为者,至矣。圣人以无用为基,以有用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无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机也。故知道之为用,非常用也。人气清则宁,神不离其体,气专辅其神,神气上下常相随也,可以长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气为体。天真者,元性也。心以性为神,神以心为用,其动在机。机动则万化应,应则荡,荡则著于欲,著于欲者为情,情生则神亡其真,故神气不可离也。人能以空入性,混于杳冥,寂然而起,则运用变化,全其妙矣。应静而静,静中有神,应寂而寂,寂中有真,此之谓也。观此数十语,至理尽矣;养生之要,不外是矣。
庄子言知北游玄水,问无为谓曰:“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无为谓不答也。又问狂屈,狂屈曰:“唉!予将语若而忘之矣。”又问于黄帝,帝曰:“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始得之矣。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与少林之门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独无言,初祖以为得吾髓,三十一菩萨各说不二法门,至文殊独曰无言说,离答问,而净名独默然者,盖一道也。古今之妙理,岂有二哉?欲涉拟议,则已去道远矣。仲尼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此无言之言,非复问答也。呜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
人能静坐,回光反照,不生种种念虑,则本来面目应时自见,何在将心役心号为修证而后得之?所谓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惟达者能通性命之情;微圣人,孰知死生之说?
佛云:“圆觉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圆觉自性也,而性非圆觉也。圆觉,性所有也;谓圆觉为性则可,谓性为圆觉则执一而废百矣。性无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圆觉与善岂足以尽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为逆境,而子舆子曰:“得者时也,失者顺也,以失为顺,则世间忧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谓是悬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此正觉所谓当于结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问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力殊言:“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有二者,则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叶乃见百千万亿文殊,无可摈者,若真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支道林说《逍遥游》,至数千言;谢东山解《渔父》,至万余言。呜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犹为累,忘言可矣。奚以数千万言为哉?此与汉之腐儒说若稽古三万字何异?且《渔父》一篇,文理浅俗,非庄子书,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学佛者穷诸行空,已灭生灭,随顺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木清净,爱风同流,观尘成就,以此群尘迷心,从物堕于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盗淫贪嗔之过也,而亡失知见,违背圆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为道而不能远于物,难矣哉。
见闻觉知,湛不摇处,念念受熏,有何筹算。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夫妄念之缠于心,如水之逝,未尝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无时得灭。况沈著于爱欲之中,而可以语学道乎?
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证如此;然则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净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说,言下便遣,了无留朕,如水中月,不可执捉,如空中云,无所留碍。虽八万四千韦陀,谓之未尝说,可也。虽寂然无声,谓之未尝默,可也。无说无默,无亦无也;有无非无,有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学佛者云智与师齐,灭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予谓士之学道者亦然。道德识见以至于文章语言,须向古人中出一头地,方始立得脚住。
●卷八
为文当存气质,气质浑圆意到辞达,便是天下之至文。若华靡淫艳,气质雕丧,虽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识通明。心识不明,虽博览多好无益也。古人谓文灭质、博溺心者,岂特为儒之病哉?亦为文之弊也。
人之为善,须出于无心;若有心,则非为善矣。有为利而为善,有为名而为善,有望报而为善:其去为恶无几矣。
动静当要深思,得失不须先虑。
心息相依,息调心静,此摄心之至要。神气交养,气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子尝客寓楼,居楼下,市声喧杂。初若不可耐,洗心内听,一二日后,寂无所闻,盖与逃空谷者略无少异。以此自悟:能从耳根返源,则无所往而不静也。闻盖尘耳。
人而无心能使物亦无心,狎鸥是也;物之无心亦能使人忘心,观水与月,尘虑亦为之澄静也。
●卷九
学书者谓凡书贵能通变,盖书中得仙手也。得法后自变其体,乃得传世耳。子谓文章亦然。文章固当以古为师;学成矣,则当别立机杼,自成一家,犹禅家所谓向上转身一路也。
李阳冰论书曰:“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容之度,于云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耳目口鼻得喜怒惨舒之态,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阳冰之于书可谓能远取诸物,所养富矣。万物之变动,造化之生成,所以资吾之用者亦广矣,岂惟翰墨为然哉?为文亦犹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