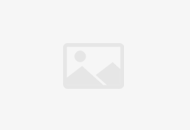祁文山的个人简介
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基本内容
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1997年6月26日凌晨3点30分,走完了他80年的人生历程
父亲祁文山:一直"潜伏"到1968年的中共党员
我的父亲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17-1997),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副主委兼秘书长等职。父亲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是和党的隐蔽斗争史紧密连在一起的。
一、投身革命前后
我家祖籍天津,1917年4月,父亲出生在天津市侯家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5岁父母双亡。为了生计,1931年父亲随他在道清铁路当工人的三哥到了河南焦作。
1932年父亲到焦作扶轮学校读书,1933年加入CP(青年团)。1934年,在党组织的资助下,父亲考入焦作扶轮中学,并被选为学校学生救国会委员,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6年元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中共豫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下党支部,该支部直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父亲任组织委员,支部成员有赵尚志、徐骏,当时领导同志有刘子久、王志杰、席国光、王吉仁。当时父亲只有20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宋弟弟"。洛阳是敌占区,为了党组织的安全,就以家庭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父亲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当小弟弟,还有两位地下党同志装扮一对夫妻,父亲称他们姐姐、姐夫,这个特殊的家庭就是当时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机关。来往信件收信人都是假名,李冷收就是给中共省委的信。后来,"姐夫"牺牲了,姐姐解放后到广西某高校任党委书记。大约是1938年11月20日左右,豫西特委指示父亲迅速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执行秘密护送任务。父亲利用在陇海铁路运输便利条件,很快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任务是护送从延安来的名叫胡服的首长。父亲说首长身材瘦高,穿深蓝色大衣,南方口音,和蔼可亲。他询问发展党员情况和组织活动情况,父亲向首长汇报他在陇海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首长听后很满意,说铁路工人是产业工人,是革命主力军,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父亲大约于11月28日把首长平安护送到河南渑池兵工厂。回到洛阳后父亲向豫西特委领导汇报了情况,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遵照刘少奇同志指示,父亲在先进铁路工人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并继续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后来父亲担任了中共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书记,并代表洛阳铁路地下党到河南的革命根据地确山县竹沟,当面向彭雪枫同志汇报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逐渐由抗战转移到反共反人民。针对此种情况,党组织决定,有计划地把思想先进的青年工人分期分批向延安转移,将党员和青年转移到军队去。当时,父亲动员组织不少青年去了延安。父亲是1939年2月春节后最后一批去延安的。
1939年6月中央组织部派父亲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党校三十二党支部委员。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的中央党校实习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1941年春天实习结束后,中央组织安排我父亲到延安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在学院里,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并多次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课。
二、潜伏生涯(一)
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父亲到中央社会部报到,报到后便送他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负责教学任务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知姓名,学员之间也互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党的特工人员,将要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事收集日伪军事情报工作。我父亲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于是中央社会部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决定我父亲结束学习,开始工作,正式成为中央社会部特工人员,并授予苏联红军参谋部上尉军衔。
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同志共同与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敌占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并详细交待了任务和组织纪律。要求父亲只能与这位社会部负责人单线联系,受他的直线领导,不得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这次派出的任务是:到东北哈尔滨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取到地图与详细的图纸。如果日本侵略军北进,可能会进攻苏联,父亲就去秘密爆破指定目标,以破坏日本侵略军进攻苏联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伪满洲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工厂。如果日本南进,另按其他方案行动。社会部部长交待任务后命令父亲要坚决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并要求他自己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个人的身份。还教他怎样寻找党,寻找八路军回根据地,寻找苏联红军等方法,比如必须找县团级以上干部,并且以中央社会部负责同志派出的特工人员的身份,同时签上隐名和真名才能与中央联系恢复关系。(父亲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后来父亲就是用这个方法与中央联系上的。最后这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你这次远离党,单独执行任务,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到白区后要组织一个家庭,有家庭作掩护,会更安全,更好为党工作。你已经25岁了,要找一个工人或者贫农出身的女子,她永远不会背叛你,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千万不要找洋学生。"
父亲按照党的指示于1941年11月离开延安出发到敌占区单独执行"潜伏"任务,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历时三个多月,父亲于1942年2月到达敌占区北平,准备过"关",执行特殊任务。后因局势发生变化,日本进攻目标由北进改为南下,爆破任务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父亲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在长期远离党组织的情况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单独秘密地执行并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5年,父亲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中央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父亲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是: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父亲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父亲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解放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掩护、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妈妈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农村长大的女孩子真的太难了!此期间,父亲以他在铁路任职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不断地将敌占区的军需物资辗转运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解放区,多次护送和掩护我党重要干部过境。1945年,蒋介石到了新乡,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吃饭。这里是我党地下情报站。当时有人提出,让一狙击手隐藏在房顶,趁其不备击毙蒋。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说我们共产党不搞暗杀。后来,父亲的意见得到中央首长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我们家这个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另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等几个交通分站,都由我父亲负责。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解放后任焦作市长)和刘得仓(新乡法院院长)。我叔叔祁士义(解放后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叔叔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有一次,情报站的交通员浚县的崔配喜伯伯,在去解放区送情报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敌人照他后脖颈砍了几刀,把他扔到荒郊野外。后来崔伯伯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只手拖着头,一只胳膊艰难地爬到了解放区……还有一次,解放军就要攻打新乡市,国民党军队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正当我们暗暗额手称庆时,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我母亲带着只有五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去“逃难”。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黑又闷又热的闷罐子车里,一路受尽苦难,我年幼体弱生病拉肚子,险些丧了小命。这个军事情报站,由于我父亲母亲和叔叔们的掩护,直到解放也没有暴露。由于军事情报及时、准确,冀鲁豫社会部授予我父亲“二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三、潜伏生涯(二)
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父亲将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我们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全家就留在了河南。与此同时,组织还决定,我父亲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潜伏”下去,而且我们家继续做隐蔽侦察点,母亲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做掩护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们甘愿以灰色面目出现,继续隐蔽潜伏下来。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对父亲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当时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察科长是石英才(后任山西省公安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叔叔“提审”我父亲,与李孝康局长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爸爸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
然而,我们全家在社会上却是“反革命特务家庭”,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袭击,街道的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我们全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放出”。父亲回到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爸爸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过了好一会我才认出爸爸,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爸爸妈妈都流泪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父亲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隐蔽侦察点。后来,公安机关在新乐路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小房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我公安机关隐蔽工作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为父母亲和他们战友们继续潜伏隐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我家由建国前的党的地下情报站延续到建国后的党的隐蔽侦察点。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各自公开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夜间到我家开会。我朦朦胧胧记得,他们每天来得都很晚,大都在我们睡下后悄悄到最里面的房间。这个小屋充满了神秘感,因为在大院里人们只能看到四间房,只有进到我们客厅里才能看到这个小屋。小屋里面放有当时很高档的办公桌椅、书架、茶具、收音机,墙上挂有地图。平常锁着门,而且门是全封闭的。爸爸妈妈和叔叔们工作到很晚。有时,半夜爸爸常过来给我们盖被子,喂水喝,他们还在工作。根据当时斗争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门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领导人是我父亲;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爸爸代号是“112”。他所领导的下属隐干也都有代号。他们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共和国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暴乱爆炸暗杀等政治案件,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后来,到了上学的时候,那些领导们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了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受到的种种歧视。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么叫成分。有一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才说:“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1956年,国家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党的指示,父亲作为可改造好的“资本家”代表“带头”加入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同时父亲为党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团结了一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商业者。
三年困难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父亲每天晚上在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天晚上我们都和爸爸妈妈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国际歌》,当唱到“要为真理而斗争……因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我看到父亲眼里闪着泪花,还充满深情地打拍子当指挥。当时我想,一个资本家唱起《国际歌》怎么这么动情。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国家公安部决定派父亲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公开身份隐蔽潜伏下来,执行一项更艰巨、更危险、更重要的任务。
1963年,公安部派父亲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公开身份为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有一天,接到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还有皇甫书信、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才知赵伯伯也曾在洛阳搞地下工作,而且与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绍入党。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他们互不认识。赵伯伯关切地问我爸爸级别与有关待遇问题,说道:33年入团,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级别太低。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交给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特为父亲提升二级,定为12级。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负责发放。
“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星期日回政协,因爸爸公开身份是资本家民主人士,随时随地都有被批判或问讯事情发生。我天天提心吊胆,到政协见到爸爸才放心。
后来,大批老干部被造反派揪出。我父亲作为河南省最高级别的“隐干”,自然是被斗的重点。因我父亲在苏联红军学院学习过,被定为“苏修特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罗织各种罪名,造谣、陷害、诬陷我父亲,致使他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有一天我回家,看见爸爸头发很长,穿件褪色蓝衣服。父亲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当时形势发展深感不安,他意识到他的中共身份有可能暴露,十分和蔼但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好像也是向我交代什么,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我一下懵了,资本家爸爸怎么是共产党员,多少年的委曲一起涌向心头。都到这个时候了,爸爸还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已得知有一个人忍受不了压力,泄露了党的机密,把父亲和一批隐蔽干部暴露了。我的父亲摘下了“资本家”的帽子,又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党员”、“特务”、“黑线人物”帽子。当时,军管会掌握了公安厅的大权,他们不知道有党的隐蔽工作这条战线,公安厅长王一鸣伯伯被批判关押,给他们解释甚至辩论,他们根本不听,还说我父亲他们是“资产阶级别动队”。于是,在全省各地深挖特务“隐干”,就这样,河南省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隐蔽干部全部被暴露。
父亲于1968年结束了他潜伏生涯。他的中共身份公开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省政协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个资本家怎么忽然变成了共产党员。不少党员干部去找他谈心,说对不起,以前对他的态度恶劣。父亲和蔼地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做得对,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亲保护起来,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战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亲最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经与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中间有父亲介绍入党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还有同父亲在延安住在一个窑洞的中央党校同学,马列主义学院同学,苏联红军学院的同学们。由于父亲搞隐敝工作,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过。只有国家公安部席国光副部长知道爸爸的隐蔽身份。这些战友大都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文革”中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因一时找不到父亲,没有证明人,有的被说成是假党员、特务等,吃尽了苦头。随着我父亲身份公开,外调人员才找到了爸爸来证明。在那个年代,父亲不畏强暴和恐吓,挺身为他们写证明材料,使他们一一获得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专题纪录片上题词时指出:“能为党的事业受委屈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1992年,父亲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祁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