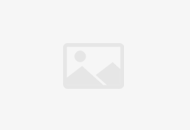切利比达克的个人简介
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ibidache,1912-1996),20世纪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指挥大师之一,生前因个性桀骜不驯以及对于录音极其吝啬而饱受争议,身后却声名鹊起、自成一派并受到广大乐迷的追捧。切利年少成名,32岁即接替因政治原因不得不暂时离开指挥台的指挥巨擘富特文格勒临时担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一职,后辗转出任瑞典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1965-1971)、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1971-1977)等职务,1973到1987年还担任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指导。1979年起,切利担任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直至去世。
生平简介
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罗曼市。其父为一地方行政长官。个性十分强悍的切利10多岁因为和父亲意见不和,就只身一人离开了家乡出外闯世界。在巴黎和黑人一起玩过一阵爵士乐后,切利来到了柏林,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为躲避兵役,进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并同时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数学等课程。在这段期间,他曾撰述关于普雷地方约斯昆音乐的论文,并曾与柏林广播乐团合作在指挥竞赛中获奖。
二战结束之后,柏林百废待兴,而柏林爱乐乐团的主人富特文格勒却因为“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盟军审查。 一阵机缘巧合,使得政治清白而又在指挥台上崭露头角的切利进入了乐团经理的视野。1945年,临时接替富特文格勒出任柏林爱乐总管的列奥·博查德(Leo Borchard)意外身亡,于是年仅32岁的切利意外成为了这个世界顶级名团的领军人物――而切利也不负重望,在职期间与众乐团成员齐心协力,不仅维持了乐团原有的演奏水准,还大大扩充了乐团的演奏曲目。1952年,富特文格勒解禁,切利让位。然而,由于性格上均争强好胜,富特文格勒对于切利一直心存芥蒂――两年之后,乐团在富特撒手人寰后选定当时声誉日隆的卡拉扬接任常任指挥,切利随即卸任并离开了柏林爱乐乐团。
此后切利开始在北欧地区继续自己的指挥生涯,1963 年他受聘担任了新组建的瑞典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同时还兼任了丹麦广播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 70 年代中期,他又开始在法国和德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1975年到1976 年,他是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1976 年到1977年,他又接过了德国南部广播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职务,此后他便经常以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为中心,广泛地开展他的指挥活动。进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后,他又将他的指挥活动扩大到了世界的范围内,在这十几年里,他先后在中美洲的一些国家的交响乐团以及美国的许多交响乐团中担任客席指挥,获得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并且还赢得了“著名乐队训练家”的美誉。
1979年,已经成为指挥大师的切利终于找到了能够达致自己音乐理念与梦想的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大师在该乐团担任音乐总监直至去世,并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珍贵录音与现场音乐会。
切利与柏林爱乐
切利指挥的第一个正规乐队就是1945的战后百废待兴的柏林爱乐乐团――其时身为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指挥天皇福特文格勒遭到盟军起诉,被暂时剥夺了指挥权,而乐队的临时指挥也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被美国大兵枪杀。同时几位德奥籍指挥大师,战时留在德国境内的如福特文格勒、伯姆、卡拉扬等。都在接受盟军的“调查”。战时出奔海外的如老克莱伯、克伦佩勒、塞尔、克纳佩布什等,不是已在外小有成就,就是像克伦佩勒一样陷入颠沛逆境中(不过能够像克伦贝勒当时一样悲惨的还真不容易)。如克利普斯则为苏俄占领区所任用,而如瓦尔特因为其犹太籍的尴尬身分,所以只有早早去投靠托斯卡尼尼了。总之,当其时留在国内的大师多被控以亲近纳粹而强制赋闲在家,跑去国外的大师则肯定是一时三刻不会回来了。所以切利则凭着自己清白得不能再清白的身份以及天分登上了柏林爱乐的宝座。
担此重任的切利,此时可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凭着其天纵的才能、灵敏的双耳,将柏林爱乐之音色磨光打蜡得洁净透明,令人几乎听不出一丝的杂质。而所谓“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份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并不是指一个人的天份只要百分之一就足够了而是指他所作的努力,甚于其天份的九十九倍,切利即是此一代表。他在柏林爱乐任内,可说是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投入指挥这项工作。他不但不断地扩充柏林爱乐的演出曲目(包括了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及许多其它二十世纪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其长时间的读谱钻研与无止境的曲目排练,也使柏林爱乐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演出。作为1945年战后重整期,到1947年福特文格勒重返乐坛这段期间的柏林爱乐指挥桥梁,切利的表现不只是称职,甚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在与乐团团员一起等待大师归来的这段岁月,他全心投入音乐,吃苦耐劳的精神,无形中给予团员一种稳定军心的力量。他对于乐曲干净精确的强烈要求,每场音乐会之前不断地演练准备,不仅让乐团演奏水准始终不坠,也令团员们忙得无暇去为音乐以外的事物烦心,而多少避开了战后仍不稳定的局面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同时切利还为了福特文格勒的提早结束非纳粹化审查四处奔走,1947年福特文格勒重掌柏林爱乐的兵符时,切利只说了一句:“博士,这是您的乐队,现在完璧归赵!”事实上,当时的切利肯定也是福特文格勒的崇拜者。其受福特文格勒的影响相当深远。须知战后渐渐步向暮年的福特文格勒。正以其对作品深邃的洞察理解,与对人生的深沉体悟,刻划出一场场撼动人心的演出。在他手中指挥棒的每一颤动,都直指着音符与音符背后所隐含的讯息。这时的福特文格勒,已臻于一指挥其内蕴最广邃圆熟之境地。此时的切利比达凯与大师朝夕相处之下,耳濡目染之余,怎能无受其丝毫感召!何况切利以其对音乐永不知足的追求、对自我几近完美的苛求,在深深为大师的音乐魔法所感悟之下,又如何会有一刻放弃向大师学习的丝毫机会!所以说切利与福特文格勒共事的这段柏林爱乐时期,可谓他一生中最大的跃进。其此生的传奇,也当是奠基于此。
但是这种美好的合作并不长久。首先福特文格勒对年轻人的才华并不是那么能忍受。再加上切利总是出言耿直,有什么说什么,两人在乐队管理方面又分工不清,摩擦很快就起来了。于是到了1952年,切利就基本没有指挥过柏林爱乐演出了。此时当时德国的另一颗指挥新星卡拉扬气势早已抬头。虽然福特文格勒一样也不喜欢卡拉扬,但却允许他出任柏林爱乐的客座指挥。再加上切利排斥歌剧(他认为歌剧是儿戏)和录音(罐头),指挥时也对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柴可夫斯基着力更多,于是被乐团里占大多数的保守派深为不喜。而另一头卡拉扬凭着圆滑的个性终于在1957年福特文格勒逝世后击败了切利,成为了福特文格勒的继任者!卡拉扬的时代从此开启。
切利再回到柏林爱乐,已是九二年的暮春,应当时德国总统的邀请。据王立德先生在古典大师一书中所述:“岁月将指挥台上的切利比达克转换成慈祥的长者,微笑着指导晚辈们如何传达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乐想。团员们对他恭敬有加,全心卖力地演出。切利比达凯坐着指挥,精灿的目光盯着乐团不放,冷静地“看”着眼前的音乐一层层地开展。他心里有一幅清晰的作曲家的音乐建构图,他将它缓缓地张开,凝聚成时间的建筑。卡拉扬挡住了切利比达凯三十多年,切利比达凯却一夕之间将柏林爱乐变回他所要的音色――“洁净透明”。
不像我们的卡大师日后那般地飞黄腾达,彻底与柏林爱乐绝缘后的切利,便辗转于世界各地客串指挥。从1954年直到1979年“定居”于慕尼黑爱乐,这二十五年间,切利比达凯于欧、美、日本等地担任客席指挥,并先后于斯德哥尔摩广播交响乐团、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斯图卡特广播交响乐团、汉堡交响乐团等处任常任指挥,直到 1979 年出任慕尼黑爱乐的音乐总监,才有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头衔。
艺术理念
在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中,切利比达克一直奉行艺术至上、理想第一的信条、在外间各种压力面前毫不妥 协。因此当初无缘继续执掌柏林爱乐,于他并非憾事。“斯图加特时期”也好,“慕尼黑时期”也罢,皆是人生流程,他执着的是音乐,并且进一步认为一流乐团为盛名及固有风格所累,未必能透过表面效果达到“真实”,不若“未受沾染”的一般演奏者单纯,能接受他的理念而直见本性。这观点与切氏深谙禅宗不无关系。禅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切氏总要乐手去除杂念,在一种“真空”状态下开始演奏。为达这一目的,他总以多得惊人的排练次数使乐团演奏达到熟而精、精而化的境地,这种象极了禅修的排练方式使这个指挥家同时获得了排练大师的雅号。
他自己也曾说:“排练是一连串的u2018不是u2019,最后可能会有一次u2018是u2019”。而且他认为排练的次数取决于乐团的素质,乐团越好,其潜力就越大,排练的次数就应该越多。因此乐团常被“排”得很惨,往往团员个个精疲力竭,只见切老仍不厌其烦地交代团员们乐曲中各个音符的“正确位置”。事实上,切利曾说过排练与正式演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音乐的探索,只有前一次排练与后一次排练的区别,因为,后一次必须做得更好!
他对每次演出的效果并没有什么预想,而是看当时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觉得音乐不是由经验来决定,音乐就是音乐,它是超越经验的。由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切利在乐团前并不是在“指挥”一首曲子,而像是在“解剖”一首曲子,而且还兴致勃勃地邀请乐团的每一个人一同参与。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会发现切利时开启了超验主义先河的指挥。
不知有人是否注意到在切利身后,EMI为其发行的唱片的一角,都印有一个红色的符号,其实中国人对它不 应会感到陌生。它频繁地出现在建筑、书籍、服装和美术作品中。只是见之者不少,有深刻印象者却不多。这符号乃是出自中国民间艺术的字形变体图案――“寿”。这吉祥符不仅是祈愿和祝福、且更是永恒的象征,也恰好是切利指挥艺术的最有力标志,同时它也蕴含着切氏的艺术与东方美学的微妙关系。
有意思的是,使其首先获得知名度的,却是他对录音的排斥,他讨厌现代录音工业把音乐裁得七零八落再重新整合的录音方式,认为音乐是活生生的、瞬间的艺术,有其独立的呼吸空间,所以他把唱片叫作“罐头”,听唱片则是和照片上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恋爱。尽管他的看法未免极端,但理智告诉我们,它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音乐演绎者所从事的主要艺术活动是现场演出,他们之所以伟大,演出的成败是最主要的评价标准。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现场演奏具有不可重复性,而唱片是经多次反复录制多工序生产而成的商品,而且听唱片最欠缺的是人与人直接的交流,由此,切氏的观点便不难理解了。诚然,以这样的观点去与飞速旋转的现代经济巨轮下的音响工业体制相对峙,确是“太不识趣”了但也正是这样的“堂·吉诃德”才得以率先进入艺术圣境,但我们要认识他,居然还是要靠制作精良的录音制品(EMI版的慕尼黑时期的录音都是乐团作为资料自己录下来的。切老在世时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近,而他自己则一次都没有听过。),切老在天有灵,怕是要与我们一同尴尬了。可见他观点如何激烈,最终也末能打破这现实。然而这一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还是使我们有机会感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并且对其艺术观、其为人及录音与音乐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
独树一帜的指挥风格
“慢,太慢!”这是许多人对切利演绎作品的第一印象,也是抱怨最多,疑惑最多的一点。其实切利早年, 多的是速度奇快、火花迸射的青春化演绎。人到晚年,锋芒内敛,作品有了长者的宽宏仁厚,从容练达,速度自然放下来,这点较易理解。且有这一倾向的,决非切氏一人。快慢是相对的,单就技术角度而言,速度最重要的是控制得均衡。而更重要的是,随学养及人生境界的递升,切老对艺术有了更深更透彻的理解,方法也相应地有了转变:对总谱作微观式研究,排练作显微化处理,一个小节甚至一个音符皆有自身生命,绝不显得匆匆草草。更为独特的是,切氏对交响作品各构成因素皆等量齐观,处理时平均用力,对经过句、装饰音也毫不放松,所以这样的慢是有着充分理由的。绝无刻意,更不是哗众取宠,而且他的慢,慢得舒缓、柔韧、松弛而富于张力,你听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漫步”主题,让你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施施然进入画卷,一切行止皆以慢动作完成,一切观瞻又都在慢镜中呈现,连听者也成了观者。再听“基辅大门”一段,慢得有力,慢得崇高,重音向四方延展,最终超越了空间的局限,每每听到这里,我都会想:到底是他的音乐太慢,还是我们的时代太快呢?惯于生活在喧嚣中的我们,惯于在快餐文化中吸收营养的我们已无法放下心来去咀嚼切老奉献给我们的音乐盛宴,而他的慢,是其艺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也是他的艺术观不可缺的重要因素,它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音乐,也进入了一种以未有过的聆听状态,慢,即是时间也即是生命的延长,这不就是寿的一种表现吗?
当然,要理解他的慢,便不得不说到他的“淡”了,切老嗜吃,大鱼大肉,但音乐却是斋素。听他的演绎,有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超然,平和、素雅中却蕴含着绵绵不绝的内力。乐音中没有渣滓,织体极为透明,真如蓝焰般的纯粹,对音乐的阐释没有夸张和矫饰,更别想找到刻意营造的“甜美或火爆”,要寻求感官剌激的乐迷们怕要失望了。他与杰西·诺尔曼的合作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时就要求这位著名的女歌唱家声音尽量不要太嘹亮,但是演出后仍然不满意,忿忿不满“这哪是维也纳的春天,充其量是蒙古的春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和歌唱家合作过了。从这也可印证他对自己艺术观念的执着。而他的这份淡然的要求来自于其多年历炼,也来自于对禅宗的深切体悟。他的淡最能满足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却从不会满足肉体式欲望。听他的演绎,使人有安详之感,古人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是经过内心激斗后复归的平和,是对矛盾的超越,他的指挥艺术的最终目标,便是要达到无尘无染、物我相忘之境。在这一点上,东方哲学的审美观竟与西方古典音乐融为一体了。行文至此,我们怕是对切老钢琴家米开朗杰利的友谊有更深的理解了,后者琴音冰清玉洁,艺术上也有形而上色彩。从这一侧面返观切老的艺术形象会更加清晰。
也有人说,切老的音乐表现了“道”,然而什么是道?平常心是道!曾有许多钢琴家无法弹好莫扎特,这便是失却平常心之故。莫扎特的作品技巧上不难,难的是一份心灵上的平淡,天真,而切氏就有这样的平常心。这“心”不就是人的“本来面目”吗?还有很多人认为,以切氏之手法,指挥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等深沉、内在,绵长的作品较合适,而指挥激情型的贝多芬和悲怆型的柴可夫斯基便觉不妥了。对于这点,完全是惯性使然,是从“准确性”、“标准化”角度,用既定的“风格”、个性去套切氏的美学,合者用,不合者弃,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音乐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既定速度,速度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速度下所表现的东西。我们可以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指挥家演绎别国、别民族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接受切氏这一具前瞻性的观点呢?其实切老具超越性的美学观完全可以涵盖地域性民族风格和狭隘的个性观。基于此,才会产生有极强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不强调风格却自有风格的抽象化音乐。他用实践印证了音乐的实质没有门派之分,没有古今之别的见解。至于切老为何从不指挥马勒,大抵是因为马勒的作品多是矛盾的产物,尽管技术上可自圆其说,但情感表达上过于纷乱和焦虑不安,这恐怕不合切老趣味;而被切老视为儿戏的歌剧,在音乐的集中性、紧凑性和与指挥的融和度上不如交响乐,而且一部分传统歌剧情节太幼稚,结构松散,戏剧性也不如交响乐,这也是与切老圆融的音乐观是有出入的。
切利比达奇的指挥艺术历一生磨炼,到了晚年俨然是出神入化了。他有一句名言:“音乐不是美,美只是通向音乐的诱饵。音乐是真!”一个“真”字注定了切利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也是一个“真”字让切利晚年得以升华,达到了自己比较理想的境界。卡拉扬一心想融合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却一生都没有做到;而切利却是谁都不买帐,只做自己,所以能自得其乐了。两人境界之高低,我想起码在我们东方人眼里是很容易辨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