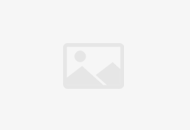孙登(魏国隐士)的个人简介
孙登(约220年~280年),字公和,号苏门先生,妙真道大宗师。汲郡共(今河南辉县市东五里固围村东二里)人。长年隐居苏门山,博才多识,熟读《易经》《老子》《庄子》之书,会弹一弦琴,尤善长啸。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于他。史书记载
晋书 列传第六十四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吴国孙权之子,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人物生平
孙登是汲郡共县人,孑然一身,没有家属,独自在北山挖掘土窟居住,夏天自己编草做衣,冬天便披下长发覆身,平生好读易经,安闲无事,常弹弦琴自娱。性情温良,从来不发脾气,有人故意捉弄他,把他投入水中,要看他发怒的形态,可是孙登从水中爬起来,却哈哈大笑,毫不介意。
后来居住在宜阳山,司马昭闻知后,命阮籍前往拜访,与他谈话,却默不作声。嵇康又跟随他游学三年,问他有何目标抱负,孙登也始终不答。
及至嵇康将离别时,对孙登说:“先生难道竟无临别赠言吗?”孙登说:“火生而有光,如不会用其光,光就形同虚物,重要的是在于能用光,光就能发生作用。人生而有才能,如不会用其才,才能反会召祸,重要的是在于能用才,才就能利益天下,所以用光在于得到薪柴,可保持久的光耀;用才在于认识获得道德真才,乃可保全其天年。如今你虽多才,可是见识寡浅,深恐难免误身于当今之世,望你慎重。”
嵇康未能接受,后来果然被司马昭所害,临终作幽愤诗,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两句,深表感慨,后悔当初不听孙登相劝之言所误。
有人说孙登认为在魏晋之际任职,容易被人猜疑,所以才沉默寡言。后来不知所终。
杨骏曾经把孙登请去,但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杨骏赠给孙登一件布袍子,孙登就要了,但一出门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两半,扔到杨骏的门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了。杨骏一怒之下把孙登抓了起来,孙登就突然病死。杨骏给了一口棺木,把孙登埋在振桥。几天后,人们却在董马坡看见了孙登。
后世纪念
道教又称孙登为孙真人或孙真人先师。长年隐居河南北山士窟并钻研易经与抚弹一弦琴。得道后又先后移居宜阳山与苏岭。传说孙登能预知未来,三国名士阮籍与嵇康都曾求教于他。
另,道教定其农历正月初三为孙登圣诞,今台湾部分道教庙宇仍会于当天祭祀该神o,谓之“孙真人先师千秋”。
历史评价
房玄龄:“①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编草,诫叔夜而凝神鉴。”“②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
轶事典故
《晋书·阮籍传》:"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后用为游逸山林、长啸放情的典故。孙登精通音律,是“啸”的最高境界的人,今河南省辉县市百泉苏门山的啸台,因其隐居于此,并“长啸”山林而闻名。
在余秋雨先生的《寻觅中华》千古绝响中有对孙登和阮籍的精彩描写,如下: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催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阮籍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疾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