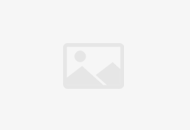伤寒玛丽的个人简介
“伤寒玛丽”,本名叫玛丽·梅伦(mary mallon),1869年生于爱尔兰,15岁时移民美国。起初,她给人当女佣。后来,她发现自己很有烹调才能,于是转行当了厨师,每月能赚到比做女佣高出很多的薪水。玛丽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 1...名称由来
“伤寒玛丽”,本名叫玛丽·梅伦(mary mallon),1869年生于爱尔兰,15岁时移民美国。起初,她给人当女佣。后来,她发现自己很有烹调才能,于是转行当了厨师,每月能赚到比做女佣高出很多的薪水。玛丽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
1906年夏天,纽约的银行家华伦带着全家去长岛消夏,雇佣玛丽做厨师。8月底,华伦的一个女儿最先感染了伤寒。接着,华伦夫人、两个女佣、园丁和另一个女儿相继感染。他们消夏的房子住了11个人,就有6个人患病。
房主深为焦虑,他想方设法找到了有处理伤寒疫情经验的专家索柏(soper)。索柏将目标锁定在了玛丽身上。他详细调查了玛丽此前7年的工作经历,发现7年中玛丽更换过7个工作地点,而每个工作地点都曾暴发过伤寒病,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1例死亡。
于是,索柏想得到玛丽的血液、粪便样本,以验证自己的推断;但这非常棘手。索柏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找到玛丽,“尽量使用外交语言,但玛丽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她抓起一把大杈子,朝我直戳过来。我飞快地跑过又长又窄的大厅,从铁门里逃了出去。”因为,在她那个年代,“健康带菌者”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她自己身体棒棒的,说她把伤寒传染给了别人,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
后来,索柏试图通过地方卫生官员说服玛丽。没想到,这更惹恼了这个倔脾气的爱尔兰裔女人。她将他们骂出门外,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
最后,当地的卫生官员带着一辆救护车和5名警察找上门。这一次,玛丽又动用了大杈子。在众人躲闪之际,玛丽突然跑了。后来,警察在壁橱里找到了她。5名警察把她抬进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医院检验结果证实了索柏的怀疑。后来,玛丽被送入纽纽附近一个名为“北边兄弟”(north brother)的小岛上的传染病房。
但玛丽始终不相信医院的结论。两年后,她向美国卫生部门提起申诉。1909年6月,《纽约美国人报》刊出一篇有关玛丽的长篇报道,引起公众一片唏嘘,卫生部门被指控侵犯人权。
1910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解除对她的隔离,条件是玛丽同意不再做厨师。1915年,玛丽已经被解除隔离5年,大家也差不多都把她遗忘了。这时,纽约一家妇产医院暴发了伤寒病,25人被感染,2人死亡。卫生部门很快在这家医院的厨房里找到了到玛丽,她已经改名为“布朗夫人”。
据说,玛丽是因为认定自己不是传染病源才重新去做厨师的,毕竟做厨师挣的钱要多得多。这次,公众对玛丽的同情心彻底消失了。玛丽也自觉理亏,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小岛上。医生对隔离中的玛丽使用了可以治疗伤寒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病菌却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治疗过程中,玛丽也渐渐了解了一些传染病的知识,甚至成了医院实验室的义工。1932年,玛丽患中风半身不遂,6年后去世。
后来,玛丽·梅伦便以“伤寒玛丽”的绰号留名于美国医学史。今天,美国人有时还会以开玩笑的口吻称患上传染病的朋友为“伤寒玛丽”。由于故事中的玛丽·梅伦总是不停地更换工作地点,因此,对于那些频繁跳槽的人,也会被周围的人戏称为“伤寒玛丽”。
逝世情况
伤寒玛莉1938年11月11日死于肺炎而非伤寒,享年69岁,推测感染肺炎的原因是死前六个月中风导致她瘫痪在床。然而,验漆崛捶⑾炙牡抑杏行矶嗷钐迳撕司藕∽钺嵩诓祭士怂沟氖ダ酌赡乖埃Saint Raymond’s Cemetery)火化。
小故事
当G·索伯博士又一次见到繁星一般遍布于尸表的玫瑰疹时,立即联想起马格丽特·米龙那双灰绿色的眼睛,清晰得如同辨认一枚独一无二的钻戒。
“那个女人,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记述她所传播的案卷整整塞满了两只大号铁柜,除一部分被收进传染病医学专著以外,其余的全被锁在纽约市卫生局的地下室里等待着销毁年限。另一只密封的箱子里装着她被抓住前的随身物品:几件式样呆板的针织上衣,一本用爱尔兰方言和意大利暗语写成的菜谱,一条俄罗斯披肩,一本袖珍版圣经。
在抗生素发明以后,全世界每年仍然会有五十万人因感染沙门氏杆菌而死。1907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纽约人发现他们正陷入和无知的俄罗斯人、墨西哥人、中国人一样的境地:伤寒病正从长岛附近向市区蔓延。自打玛格丽特·米龙象胡迪尼一样逃脱隔离医院,消失在这座带有索引的庞大迷宫里之后,东北部已经连续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的伤寒流行。这一回纽约卫生局的工程师们几乎凭借着直觉,在曼哈顿公园区大道将刚刚受雇厨娘的“伤寒玛丽”抓获,“你只需要打听附近谁家有最好吃的烟熏鲑鱼就行了”。在1910年的听证上,纽约公共卫生主管索伯博士是释放这名免疫伤寒带菌者的最激烈反对者,最高法院在要玛格丽特向上帝发誓不再从事接触食物的工作后,当庭将她释放。四年后,索伯在新一轮传染病爆发之前,在新泽西韦斯切斯县将再度找到了重操旧业的玛格丽特,终于如愿以偿地永远将她关进了北方兄弟岛。
玛格丽特·米龙一生中直接传播了52例伤寒,其中7例死亡,间接被传染者不计其数。美国政府拒绝认定她的国籍和出生地,1932年她由于中风瘫痪,死亡时大概68岁。在同一间玻璃笼子里,除了短暂的间歇,前前后后一共被关了二十七年。
后世的评论
玛莉造成的问题部份乃肇因於她不顾一切地否认自身的处境,即使身上带有足以致命的病原体,她仍保持健康状态,且毫无感染过伤寒的纪录。但是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美国歧视工人阶级的爱尔兰移民,对於此一事件也不可免责。过去有段时间,人们以「伤寒玛莉」称呼类似玛莉·马龙这种身为带原者却拒绝采取适当防范措施的人,由於该词具有部分歧视、讽刺意味,今日一般通称带有病原体却无症状的人作「带菌者」。
中国版伤寒玛丽
"伤寒玛丽"有翻版 保姆体检不能省
谢某不满3岁的女儿突然出现了厌食、咳嗽、精神不振等症状,谢某夫妇赶紧把女儿抱到医院检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女儿患了肺结核。可夫妇俩从没得过这种病,怎么会传染给女儿呢?原来,保姆患有结核病。谢某夫妇为此后悔不迭,他们说,当初由于抽不出时间,所以没带保姆做体检。保姆对孩子很好,而且看了一段时间孩子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把体检的事抛在脑后了。
这件事不禁让人想起国外的"伤寒玛丽"事件。玛丽是一名家庭厨工,就相当于我国目前替主人买菜做饭的钟点工。她看上去身体健康并无疾病,10年中她先后为8户人家操厨,造成伤寒杆菌污染食物,导致200多人相继患了伤寒。10年后才引起雇主和卫生部门的警觉:怎么玛丽到哪里操厨哪里就有伤寒病发生?卫生部门给她一检查,原来玛丽体内潜藏着伤寒杆菌,但她本人却无任何症状,她成了长期的"病原携带者",一旦玛丽与别人密切接触,就能将体内潜藏的伤寒杆菌传染给周围健康的人们,让别人患病,而她自己则安然无恙。
保姆是与家人"密切接触者",如果保姆患有某种传染病或是某种传染病的病原携带者,很可能将传染病传给健康的家人,而且保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抵抗力极弱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老人,传染疾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目前,我国的保姆劳务市场虽然很大,但对保姆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有:(1)雇主缺乏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或者是因为工作忙,或者是认为花钱给保姆体检不值得。(2)保姆的抵触情绪。有的保姆认为要自己体检是对自己的歧视。其实这是一个健康误区,就算是公办幼儿园里的保育员和老师,每年也必须进行健康检查才能上岗,她们查出有病时必须另换工作。(3)职业中介机构也未开展这项工作。
那么,保姆查出患哪些疾病就不能上岗服务呢?(1)病毒性肝炎及病毒携带者;(2)痢疾(包括阿米巴痢疾、细菌性痢疾及带菌者);(3)伤寒及带菌者;(4)活动性肺结核;(5)化脓性、渗出性皮肤病及接触性传染的皮肤病患者(如脓疱疮、疥疮、股癣等);(6)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如重症沙眼、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性病等)。
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带你家的保姆或钟点工去做完健康体检后再上岗,切莫怕麻烦或者为了省几个小钱,而给孩子或家人埋下健康隐患。
文化隐喻
190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生物学会的会员们被告知,第一例已知的"慢性伤寒菌传播者"或"健康带菌者"被发现。这个"带菌者"的名字是玛丽·玛尔伦,一个爱尔兰的女性移民,她的职业是一个家庭的厨娘。这个不幸的女人将背上"伤寒玛丽"的恶名受到追踪、注意和调查。于是,在这个偶然发现的"带菌者"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控制和"带菌者"的两种叙事,并生成了一个探讨和利用这一事实且特征和特性清晰可辨的特殊故事。在政府卫生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明处荼毒人口、暗中威胁社会秩序的传染疾病。为了社会的健康,医学群体和媒体联手合作,媒体支持的医学理论将成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并为处理这一事件的正当性提供了合法的舆论和社会条件。而"伤寒玛丽"却以"无辜者"的抗拒匿名潜逃了。
"伤寒玛丽"的故事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是一个完整的隐喻。大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从来都被视为是"带菌的文化",它在夹缝中生存并腹背受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文化类型里经常含有的"不健康文化",于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它普遍流行的后果无疑与"伤寒病菌"相类似,作为文化疾病,尤其对青年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在知识分子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低俗的文化",是与学院文化和经典文化不能相提并论的文化垃圾。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再次想到大众文化与"伤寒玛丽"的相似性关系:玛丽的身份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她不是美国本土公民,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她的身份本来就是可疑的,或者说,她的"不洁"与她的身份先天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爱尔兰人",种族的问题也隐含于"带菌者"的叙述中,或者说,"伤寒病菌"是外来的,对于美国的沙文主义来说,他们顿时拥有了另一种恐慌。一位医学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从去年好几个星期到今年冬天,亚洲霍乱光顾了欧洲人民,在俄国尤其如此。每天早晨,美国的读书人、领导人、杰出的务实家,还不包括像小鸟一样早早起来翱翔的自由人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这些美国公民们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为那些遭受着痛苦的不幸者感到悲悯,他们因为无知和懒散而不得不承受痛苦。美国公民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的咖啡杯面前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些盲目的、糊涂的和迷信的帝俄农民一样无可奈何地承受和死于霍乱。这样美滋滋地思索着的美国公民在他的某个阈下意识层上搁置了或不再考虑美国的伤寒病。"在这样的叙述中,美国幻想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跃然纸上。但是,"伤寒玛丽"使美国和帝俄的农民的区别变得困难和复杂;性别歧视也同样隐含在"伤寒玛丽"的叙事中。这个爱尔兰女性因这个恶名而被妖魔化。她被描写成一个丑陋的女人,一个壮实的如同男人一样的女人,一个老处女却同肮脏的男人睡觉的女人。在这样的叙述中,"伤寒玛丽"的恶名被一再放大,于是她也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带菌者"。
大众文化的一再争论和不被信任,源于意识形态和经典文化的优越感,就像美国沙文主义面对亚洲霍乱一样。意识形态的秩序和国家民族关怀叙事以及知识分子经典文化信仰,使处于边缘的大众文化不仅在文化"等级"上倍受歧视,而且因其对文化尊严的冒犯也始终难以确立其合法性地位。大众文化一旦被指认为"带菌"之后,它动荡不定的"身份"和命运就几乎是宿命的。在学院经典文化维护者那里看来: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即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这些特征以凯旋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支撑点,并以"文化幻觉"的方式制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这些文化英雄主义的判词,使大众文化命定地成了文化结构中的丑角。然而,这一揭示对中国大众文化来说却并不全然有效。
20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或者说,不同的政治、文化诉求,都在大众文化这一领域有所表达。因此,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改造、转换,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最为经典的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在民族危亡、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先觉的知识分子要推翻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要把贵族的文学还与平民。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等,主张重建的都是"通俗行远之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和"普遍"、"真挚"的文学。这一时期的讨论隐含着明确的新文化要求和想象。它密切地联系着近代以来建立民族国家的神话和梦想。但还于平民的文化实际上是在知识分子的诉求和想象中展开的,它所表达的情感、内容以及痛苦、感伤、迷惘的情绪,与大众并没有关系。即便他们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仍然是居高临下的"乘车人"。
第二次讨论的意义尤为重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在革命文艺家内部几乎延续了10年之久,并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提供了文学理论的背景。这一方针的提出,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所遵循的准则和尺度。而这里隐含的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成为不争的共识。应该承认,上述两次讨论尽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作为主流话语达到了倡导者设定的期许。百年来中国动荡的社会处境,使所有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讨论和期待,难以诉诸于纯粹的文学范畴而不得不负载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性内容。国家民族危亡的述说和救亡的吁求在这些大众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作为知识分子或文学艺术家,也正是或只有通过这一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关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的幸与不幸全部都隐含于这一矛盾和说不清的情境之中。但是,这一情况也已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大众文化"的内涵不仅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同时它与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类型概念也不完全相同。在西方,大众文化包括多种含义:它可以是为大众的文化或出自民间的文化。在形式上,它是指歌谣、诗歌、写实的或形象生动的故事、浪漫故事或忏悔录,诙谐小说或沿街兜售的诗文小册子,西部小说、恐怖小说、科学小说或幻想故事,寓言和讽刺小品、劝善画册、连环漫画和画页,甚至图画明信片。也可以用于指某种新闻文字,还包括戏剧文学的整个领域,从独角戏、小型喜剧到未经删节的戏剧。而它的作用则是"仅供消遣",但中国大众文化的上述讨论,并不是在这一范畴内展开的。无论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它更多指涉的是一个"为什么人"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众文化的两次讨论,不仅实现了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知识分子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译"。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中国的文艺家第一次创作出了活泼健康的中国农民和士兵的形象。它对于实现战时的民众动员,让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救,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动荡时期或战时的大众文化讨论,在清除"带菌文化"的同时,它的建设性应当是更重要的。然而,这一文化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主流之后,却也带来了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农民文化及其趣味的普及。在这次讨论之后,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红色经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产生,是在1938年"文章下乡"和1942年"走向民间"的背景下完成的。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魅力啊!这种魅力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然而这里的"群众"事实上就是农民。包括《小二黑结婚》在内的一些作品,在实现了向农民文化转移、倾斜的过程中,在表意策略上也同时实现了向旧文化的某种妥协。或者说,这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在结构形式上所沿袭的仍然是"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模式。小二黑、小芹,刘巧儿、赵振华,都是在这样的结构模式中得到表达的。因此,第二次"大众文化"的讨论,其"除菌"的对象事实上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及其迷惘、感伤、痛苦的"小资产阶级"情感。二是农民文化趣味的思维惯性一旦形成便没有尽期地迟迟延宕。新中国诞生以来,对"带菌文化"的清理就成为日常性的文化政策。战时的紧张和焦虑并没有因和平时期的到来获得缓解,战时的文艺主张几乎完整地置换于和平时期。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所清理的对象,事实上都被指认为"文化带菌者"。不仅娱性的大众文艺失去了生产和存在的可能,就是严肃文艺中与人性、人情相关的作品,也都被指认为"带菌者"而遭致不断的清算。从《我们夫妇之间》到《达吉和她的父亲》,从《美丽》到《红豆》,人的正常的情爱表达都是被视为罪恶的。这种状况自然与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有关。在毛泽东看来,要反对旧文化,同时要建设新文化。但是,旧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不仅指传统的封建文化,同时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农民文化甚至知识分子文化的某些部分。而新文化却是始终不明确的,它虽然被表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期待它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但对于具体的文艺形式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符合"新文化猜想",始终是所指不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新文化是一个不断透明、纯粹、简单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样板戏"的盎然兴趣中得到证实。也正是这种透明、纯粹、简单的"新文化"要求,使农民文化可资利用的某些方面被一再放大凸现,并藉此排斥、打击、拒绝其他被视为"带菌"的文化。因此,第二次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和此后形成的文化主流,事实上也是一种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化"除菌"运动塑造的文化不再是人间关怀的文化,因此也与"大众文化"不再发生关系。
大众文化的第三次讨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语境。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关系,因此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当市场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确立之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因素便无可避免地迅速生成并疯狂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次讨论产生之前,大众文化已经在80年代的民间悄然流行。并且是港台文化"反哺"的结果。那是一个乐观浪漫的时代,社会上的各种气氛和情绪预示了国家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松弛的环境为民间多种欲望的释放提供了可能。在尚未产生本土消费文化的时候,"外来形式"执行了它的消闲功能。邓丽君在大陆的成功引发了港台文化"反哺"现象的规模展开。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的温情散文,席慕蓉的纯情诗歌以及大量的港台、新加坡华语电视剧迅速流行。这一现象几乎全面改写了大陆的文化生活和民众的文化消费趣味。被人们经常以轻蔑的态度喻为"文化沙漠"的港台文化轻易地占据了大陆的文化市场。它的被接受显然向我们传达了大众文化生产的某些内部规律,并示喻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域外对大众文化生产的丰富经验。它们以幻觉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与现实生活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它的文化内涵大众不仅熟悉,而且充满了观赏和阅读的心理期待:它们讲述的都是道德、伦理、情爱、血缘等人间关系。它不是政治家们的政治目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那些寻常事、平常心于百姓来说是"关己"的。这样的大众文化虽然含有无可回避的商业动机,然而它又确实是以大众作为关怀对象,在实现商业诉求的同时也体现了商业文化的道德意识,因此,也就以"文化幻觉"的形式实施了对大众的"文化抚慰"。这种大众文化生产的规范和成熟,与我们80年代大众文化初期生产的状况相比,它显然已经经过了"除菌"过程。但对于刚刚试图欲望释放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来说,正在经历的恰恰是"渴望伤寒感染"的未免疫期。
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阶层在这时发现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伤寒玛丽",于是掀起了第三次关于大众文化的再讨论。这次讨论略有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并规约目标的。或者说,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冲毁了传统的人文堤坝的时候,当知识分子所固守的人文精神遭致了威胁的时候,他们对无处不在的世俗生活气息不仅深怀失望,同时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迫。他们认为现实世界出现了"精神危机",人们"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于是,在一场被命名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大众文化又一次作为具体对象被提出。在这次讨论中,对大众文化以意识形态立场的"除菌"意图几乎完全淡出。精英知识分子希望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人们也能关注自己的精神处境,也能多少保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因此,这次讨论所针对的主要是"商业主义文化",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它的仿真、复制、消费和时尚号召,是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它的全部复杂性也只有在这一时代才能得以反映。精英知识分子的激进批判,虽然因其国家民族和精神关怀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但在红尘滚滚的时代事实上这一批判不仅失去了倾听者,而且根本无法改变它的疯狂生产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只有这时,我们才深刻感知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这一激进的表达只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苍凉手势,一个最后的优雅姿态。我们曾经崇拜、迷信的"大众"已经散去,时代的转型使那些可以整体动员的"大众"已经变成了今日悠闲的消费者。
但这次讨论却取得了知识层面的收获,如讨论澄清了过去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造成二者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是大众文化制造者的策略,以掩盖其文化消解性及对人的生活的反作用;一旦将大众文化说成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便可以在’我们要高雅文化,也要通俗文化’的响亮口号下堂而皇之地制造出来。实际上,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变为一种商品制作,它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而是商品性与制作性:它制造了大众的情感和生活趣味。"这个揭示的重要性在于:"伤寒玛丽"是被制造出来的,它为了取悦于"渴望感染"的趣味要求,以投其所好的方式满足了"被感染者"。
在漫长的"除菌"过程的浸润下,也同时培育了大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趣味。我们发现,中国当代文化的经典作品,事实上都有大众文化的叙述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暴力崇尚"情结。"三红两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闯王])以及《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战火中的青春》,等等,它的战斗和血腥场面,与大众文化中的暴力、仇杀叙事有极大的相似性。以至于当红色革命的暴力叙事资源难以维系再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欣赏兴趣很快地转移到了武侠小说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是大学教授,一面在课堂上讲学院经典,而在课下,腋下夹的也是武侠小说。进入90年代之后,当大众文化中的色情、暴力叙事逐渐转向历史和民间奇观以后,而恰恰在"严肃文学"或"高雅文学"中,大众文化的主要旨能得到了空前的使用。我们在《废都》、《白鹿原》、《羊的门》、《国画》、《尘埃落定》等作品中,"性"几乎是最重要的旨能,它们引起纷纷扬扬议论的主要问题也大多源于此;而在"女性文学"中,"身体叙事"已经成为批评界的共识。身体暴露是女性文学主要的表意策略之一。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无处不在具有极大的侵蚀性。于是我们就都成了"文化带菌者"。
这是一个欲望无边的时代,也是一个"游牧文化"在"千座高原"自由驰骋的时代。"众神狂欢"真的给了我们绝对的自由吗?我们在呼唤这个自由时代的同时,是否也呼唤出了妖魔?我们在"除菌"的过程中,是否自己就是道德意义上的"伤寒玛丽"?汉娜·阿伦特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文中,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表达,无情地解构了"通常叫做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公众的赞赏......常常是他们报酬的一部分......对医生来说,这要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对律师来说,所占的部分更大,对诗人和哲学家来说,几乎占了全部。"她认为,"不言自明的是,公众的赞赏和金钱的报酬属于同一性质,两者可以互相置换。公众的赞赏也是某种可姿利用的东西:地位身份"。阿伦特在这里所要论证的是,当公共论域已经开放之后,事实上,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并不相同,因此,他们的言说方式和所要维护的东西自然有别。但对于热爱言辞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伤寒玛丽"却还一定扮演"文化除菌者",为了表达我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们一定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似乎除此之外我们已别无选择。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众文化从内涵到生产策略的变化,从来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才改变的。市场作为隐形之手的控制才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发现,当下大众文化的生产,已经远离了20世纪80年代的色情和暴力,这一层面的欲望满足已经饱和。它向优雅、怀旧、戏说、家族、情爱和善恶等方向的转移当然并没有离开利益要求,但对大众文化的传统指责显然已经不再有效。用审美批评的方式对待或要求消费文化,本来就是错位的批评。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可能和大众文化一样,如果固守于一种不变的、被"真理意志"控制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会是"伤寒玛丽"一样的"文化带菌者"。但我有理由相信的是,经历了"伤寒"之后,我们也就获得了免疫的抗体,因此,我们也就不再是道德审判的"文化带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