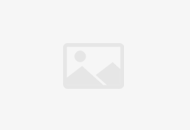孙枝蔚的个人简介
孙家世代为大商人。李自成入关,散家财组织团勇抵抗李自成,为所败。只身著有《溉堂前集》九卷,《溉堂续集》六卷,《溉堂后集》六卷,及诗余二卷,(均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aaqa清史列传)并行于走江都,折节读书,肆力于诗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官扬州,先赠以诗,称为奇人;又特访之,与订莫逆交。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举“博学鸿儒”科,因年老不能应试,特旨偕邱钟仁等七人授内阁中书。但不忘故乡,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枝蔚工诗词,多激壮之音 孙枝蔚, (1620年一1687年),清初著名诗人。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因其家乡关中有焦获泽,时人因以焦获称之。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年六十八岁。
简介
孙家世代为大商人。李自成入关,散家财组织团勇抵抗李自成,为所败。只身走江都,折节读书,肆力于诗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官扬州,先赠以诗,称为奇人;又特访之,与订莫逆交。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举“博学鸿儒”科,因年老不能应试,特旨偕邱钟仁等七人授内阁中书。但不忘故乡,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枝蔚工诗词,多激壮之音。
人物作品
孙枝蔚(1620-1687年),亦叫孙八,字溉堂、叔发,号豹人,陕西三原人,清初著名诗人。孙八一生,著述甚富:所著《溉堂集》,含《前集》九卷、《续集》六卷、《诗余》二卷、《文集》五卷、《后集》六卷,计二十八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二千余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亦为作者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诗。他成为客居扬州的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多的诗人。[
文学成就
生于明光宗泰昌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年六十八岁。世为大贾。李自成入关,散家财求壮士起义,为所败。只身走江都,折节读书,肆力于诗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官扬州,先赠以诗,称为奇人;又特访之,与订莫逆交。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举“博学鸿儒”科,因年老不能应试,特旨偕邱钟仁等七人授内阁中书。但不忘故乡,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枝蔚工诗词,多激壮之音。著有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及诗余二卷,(均清史列传)
清代初年,就北方遗民诗群的分布态势而言,关中一地基本上与山左、 畿辅 鼎足而三.这里的社会环境、人文渊源,乃至遗民社会的结构形态不仅与淮海、江南、岭南诸区域大异,而且与同处北方的山左、畿辅等地也不尽相同.自明末以来动荡反复的社会局势,使得生存于其中的关中士人,尤其是遗民的心态和人格更趋复杂化。此地士人虽以遗民自居者甚多,但其人格特征较之浙东、江南诸地遗民的强项不屈来,又略显通达.与此相关,关中遗民诗人又在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中,逐步形成了创作风格上的多元化格局。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关中遗民诗人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更为甚者,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重文轻诗,将文的创作与对理学的探究置于其整个人文活动的首位,其诗歌作品面世者本就不多,而能传至今日者则更少了.不过,就其现存诗作而言,其中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在整个遗民诗界、乃至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这里仅以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孙枝蔚为例,来剖析关中遗民诗人之创作特征。孙枝蔚(1620~1678),字豹人,室名溉堂,陕西三原人.因关中有焦获泽,时人因以焦获称之.三原孙氏,世为大贾,明末时已 行商扬州.崇祯末年,李自成兵攻人撞关,孙枝蔚散家财,结客集义勇数千相抗,几遭不测。明亡后逃至扬州经商,累致千金;后折节读书,结交四方名士,遂以诗名世。康熙十八年在京应鸿博试,不终幅而出,赐中书舍人衔,还归扬州,以隐逸终老。溉堂一生,著述甚富.今存《溉堂集》,含《前集》九卷、《续集》六卷、《诗余》二卷、《 文集》五卷、《后集》六卷,计二十八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二千余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亦为作者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诗。要充分理解溉堂诗,必须先了解溉堂其人。
一、溉堂当为遗民
溉堂因被迫参加了康熙十八年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因此,后世多将其排除于遗民行列.卓尔堪《明遗民诗》不录溉堂一诗,绝非漏收;现存各种《明遗民录》中,都没有溉堂的名字;钱仲联先生主编之《清诗纪事》,在《明遗民卷》中亦不见溉堂之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很有必要为溉堂一辩。
康熙十七年诏开的博学鸿词科,一直到第二年3月l日才开科考试。一时间,四方硕儒名士云集京城,其中有屡辞不获准而勉强应征的,也有自愿应考者。孙枝蔚显系前者.当时,陕西举荐者凡9人,李顺托辞有病、以死相抗,未至京城;王弘撰虽至京,但亦托病拒上考场;其余7人,孙枝蔚、李因笃、李念慈、李大椿、王孙蔚、程必升、赵廷用均上了考场,但结果除李因笃一人中式、孙枝蔚赐衔外,其余5人均告落第.李因笃似乎很不幸,他名声太大,荐举者多,当局必欲致之”[I]母亲也“劝之行”,推辞不过,“涕泣就道”。结果金榜有名,却不愿出仕,不得不以一份情词恳恻的《告终养疏》来请求放归,很像是下了水又赶忙往岸上爬.然而,遗民的资格就这样丢了,并且还遭到友人的谴责(亭林于《答李子德》中不仅说:“愿老弟自今以往,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则所以全之者大矣”;而且道:“窃谓足下身摄青云,当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败其晚节,则必夭其天矣。”)甚至连沈德潜也说:“圣主之仁,人子之孝,字同共称”,[2]显然微含讽意。当然,读《受祺堂诗文集》,我们又的确感受到李因笃的内心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痛隐之中。
孙枝蔚的情况更特殊.被荐应博学鸿词试时,他在扬州(豹人老友杜F闻说豹人被荐,曾有《与孙豹人书》劝其。勿作两截人,,见《变雅堂文集》卷四),并且已59岁了.屡辞不允,勉强进京,不得已进了考场,但又“不终幅而出”,也就是说试卷未答完即出了考场.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云:
……屡求罢不允,捉入试,不终幅而出。天子雅闻其名,命赐j以宠其行。部拟正字,上薄之,特予中书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试不得,至是诣午门谢,部臣见其须眉浩白,戏语曰:“君老矣,u2019!豹人正色曰:“仆始辞诏,公曰不老;今辞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辞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谢之。
《施愚山集·郑孙豹人归扬州序》、王《今世说》“孙豹人应诏人都”条、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二十九、《清史列传》卷七十一等均有类似记载。溉堂本人在《溉堂后集》卷一中的一个诗题里也这样写道:“部仪初授布衣及生员责监生,年老者六人为司经局正字,疏上,上特命进内阁中书舍人,复增未试者二人同授是官,再纪二诗。六人为王方谷、丘钟仁、申维翰、邓汉仪、王嗣槐及枝蔚,二人为傅山、杜越.”溉堂在京期间,尽管没有傅山那样倔强不屈的表现I3],但也总算勉强保住了遗民的资格。他尽管道:“拜谢须朝服,羞惭对钓竿”;但又言:“他时戒吾子,不必上铭族”。这与傅山归晋后不许家人挂匾,不许他人称其为“中书舍人”,同出一理:他们仍是先朝的遗民!溉堂于康熙十八年在京应试期间所写的不少诗歌,均流露出强烈的遗民心态。他不仅以《出处》为诗题,检查自己的行为,而且于《在京答亲友》中说:“因观自古来,吾宁守故吾。”在《咏怀十三首》中,他一方面讽刺无节行的王维,说“王维是何人,乃笑柴桑翁”;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进京行为而羞惭:“归去寻旧鹤,逍遥肆吾志。素衣今已细,顾之窃有愧”。当他得知李中孚、魏凝叔、应嗣寅等人拒不应诏时,即以《处士三人被召不至,美之以诗,各一绝》为题,成三绝句以褒扬其高风亮节。其中《李中孚》写道:“平生未识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征车拼饿死,闻风愧煞懦顽夫。”正因如此,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以溉堂人“前编”,归人遗民行列,确为只眼独具,深知溉堂者。
二、溉堂诗的认识价值
溉堂诗编年始于癸未(1643年),时当明朝灭亡的前一年,李自成的农民义军正纵横中原,满洲军队又屡叩关门。亲身感受了社会的动荡不宁,又亲眼目睹了清军人关后的残酷暴行,因此,溉堂诗中写于明亡前后的作品多忧时念乱之情。眼看大厦将倾,山河日非,诗人忧心如焚,他曾频频吟唱道:“乾坤多战血,叹息对明灯”;(《为农》)“闭户过清秋,伤时泪暗流”。(《村居杂感)))诗人甚至谴责那些拥有重兵的将领们,说他们蒙思酿祸,贻误国事。如《渔关》即云:
久失中原势,长忧臂指连。
蒙恩非一将,酿祸到今年。
竟忍欺明主,谁令拥重权。
京师根本地,谁只哭秦川。
身居秦川而心忧京师,儒生本色,令人叹怀。1644年春,清军人京,南明弘光朝立于南京。但当诗人闻说江北四镇骄横难制,南明小皇帝又大肆征选宫女、荒淫无道时,不禁又忧心忡忡。《昨有》两首便反映的是当时的真实情景,其中第一首写道:
昨有金陵信,遥传恐未真。
朝廷忧四镇,宫女盛千人。
驾驭英雄主,艰难社极臣。
万邦深属望,何日慰沾巾。
另外,《闻败军已破县城》、《除夕》、《甲申述变》、《纪感》、《甲申春日纪事》等作均对明亡前后的乱世极具认识价值。这种忧时念乱的情怀直到诗人顺治三年(1646)至扬州后仍保持着,乱后江南的衰败景象仍不断出现在诗人笔下。《春日登扬州城楼》、《登多景楼》、《姑苏舟中》、《岁暮遣怀》、《泊舟毗陵触目有述》等所呈现的仍是一幅幅乱离景象:诸如“瓜州人烟少,独行荆棘间”,“日落笳初动,城空鸟自还”,“可怜风雨夕,鬼哭满江山”(《乱后过瓜州》)之类的诗句俯拾即是。顺治九年(1652),诗人过镇江,登金山,有《乱后登金山有感》,诗云:
钟鼓仍朝暮,全身计未周。
江边人牧马,山下骨随舟。
飞鹭全无意,居僧始有愁。
何时销战甲,高枕看扬州。
白骨随舟的凄惨景象与诗人期望和平的情思交织一处,读来感人至深。
更可贵者,溉堂诗能于忧时念乱的情怀中渗人对民生的关注,着意勾画出一幅幅乱世流民图.诗人不仅在《哀纤夫》、《水叹》、《佃者歌》等篇中写天灾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常常为百姓一洒同情之泪;而且在《乌夜啼》、《空城雀》、《篙里曲》中揭示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痛苦,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扼腕叹息。《佃者歌》有一“小序”写道:“褥暑中,儿燕归自田间,述佃户贫苦状,余恻然代佃作歌。”《空城雀》云:“自从桑田变沧海,经过空城泪如泉.邻舍不知窜何处,时闻雀声噪檐前.”《篙里曲》又云:“道旁白骨走蚁虫,不如秋草随飘风。此曹有母复有妻,谁令抛置古城东。肢骸杂乱相撑柱,如汝或为雌与雄,或为壮士或老翁。”如此饱蘸同情笔墨,对乱后惨象作历历描绘者,清初诗人中尚不多见。溉堂诗实为我们了解清初民生开启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概堂一生虽然以居扬州的时日为多,但游踪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其诗作中纪游与友朋酬唱之作最多。正如王泽弘《溉堂后集·序》所言:“先生秦人也,寄居广陵,穷老无归,以谋生不暇,日奔走于燕、赵、鲁、魏、吴、越、楚、豫之郊,其所阅历山川险阻、风土变异及交友、世情向背厚薄之故,皆一一发之于诗,以鸣不平而舒佛郁。”溉堂纪游诗,或写景物,或纪风俗,或抒旅途苦况,大都写得慷慨淋漓,真情感人。如深得王士祯赞许的《舟行遇大风》写道:“风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云边。也知赋命元穷薄,尚欲西归大华眠.”诗写于溉堂游镇江焦山时,海云突变、风起中流,荡舟激流中的诗人却长啸咏诗,这是何等的襟怀气度。
溉堂交游广,但不滥.其交游范围,除周亮工、王士禄、王士祯、张晋、陈维裕、尤侗、毛奇龄、枉揖、朱彝尊、施闰章等少数一些国朝文人外,大都局限于遗民圈内.据《溉堂集》可知,经常与溉堂诗词唱和的遗民即有张养重、杜溶、方文、吴嘉纪、冒襄、林古度、余怀、黄云、孙默、龚贤、纪映钟、黄周星等10多位。由这个名单亦可知溉堂与江北遗民诗群交往尤密,可以说,作为一位关中诗人,他的诗文化活动是在江北遗民诗群中展开的。《溉堂集》中写给吴嘉记的诗有近10首,如《溉堂喜雨同于皇、宾贤、舟次》、《雪中忆吴宾贤》、《怀吴宾贤》诸篇,真情流溢,感人至深.其中《怀吴宾贤》一篇,尤见诗人性情,不妨引录如下:
重游东海上,窃喜近吴生.
十日不相见,秋风无限情.
雨余流水急,寺里晚钟鸣.
为有扁舟约,踟蹰立古城.
当然,溉堂应酬之作也未免写得太滥,如《为周子维缺唇解嘲》、《黄大宗纳妾扬州为赋催妆诗》之类,确也无聊乏味。尤其到了诗人晚年,应酬之作充峡盈卷,触目皆是,未免令人生厌。
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子,溉堂诗中还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溉堂居扬州,筑室日“溉堂”,取自《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R”,即寓不忘乡关,常怀西归之意.陈维裕《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孙子年四十余,发毵毵然白,张目不阖者如线,嗜吟酒,召之饮则无不饮,若忘其年之将老,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痪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溉堂虽居扬州,但时时操秦声,对故土一刻也不忘怀。他曾一再写道二“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溉堂诗》)“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夏日寄题渭北草堂》)“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仅据溉堂《张戒庵诗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出版之《溉堂集》中未收此“序”,见赵逵夫先生《孙枝蔚的一篇佚文与清初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文载《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可知,即有张晋、李楷、张询、雷士俊、韩诗、东云雏等数人,另外还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灿、张谦等.溉堂的思乡曲,实际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声。
作为清初遗民中一种类型的代表,溉堂诗中所反映的诗人对出处的思考及晚年所呈现的心态也有其特点.他一方面为自己曾至京师应试而不时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又与二三遗老一起自喻“商山四皓”,自坚志节。一方面孤独与凄凉不断侵袭着他衰惫的心灵;另一方面与遗民旧友的交往与酬唱又不时消解着这种孤寂.康熙十七年,59岁的溉堂老人与汪揖、邓汉仪、吴雯聚于汪楫寓所,慨堂有《夜过汪舟次寓舍,适邓孝威、吴天章亦至,因留饮赋诗》云:
老觉同心少,宵惊天气寒。
谈深关出处,坐久费杯盘。
赋似扬雄易,才如乐易难.
兵戈扰满地,莫只喜弹冠。
63岁至金陵时,溉堂又道:“阅江辛苦地,遗老独徘徊.”(《金陵》)康熙二十三年,65岁的溉堂老人又一次与朋友夜集,并有《顾书先雨中携尊过刘升如次山楼,招同杜于皇、徐松之、宗定九夜集》诗,诗云:
风雨催寒早,携车傍暮鸦.
一炉新试火,十月尚开花。
烂漫吟偏好,颠狂老更加。
商颜即此地,四皓在君家。
此诗之后有诗人自注:“坐中于皇年七十四,松之六十八,余与定九同六十五。”而《书离骚后》、《书陶诗后》、《书谷音后》诸诗,更见晚年寄托。不难看出,溉堂晚年,士人失所之后的忧伤情怀虽已淡化,但遗民本色并未改变。
三、溉堂学宋及其诗风的主导倾向
溉堂诗的作法,当时评家及后世论者均认识不一,或言宗唐,或言学宋,各持一端。王士祯任扬州府推官时,与溉堂相知,因此《溉堂前集》与《溉堂续集》中多王氏评语;而这些评语或言“似储,似杜《新安》、《石壕》诸作”,或言“从杜咏物诗变出”,或言“似太白古风”,总之认定溉堂学唐。施闰章、王士禄、汪揖、吴嘉纪等人的评语与阮亭大致相同。但是,汪懋麟《溉堂文集序》却说:“不见征君之为诗乎,最喜学宋,时人大非之.”溉堂自己在《溉堂文集》卷一《汪舟次山闻集序》中也说:“予于宋贤诗颇服膺东坡.”他作诗,仿效苏东坡者也不少,如《除夕和东坡韵三首》、《除夕怀五兄大宗次东坡韵》等。康熙十八年,溉堂在京应博学鸿词试时,仍随身携带《山谷集》,且作和诗二首。其《和黄山谷拟省题二首》诗前“小引”曰:“御试有期,同来应召诸子皆闭户研练诗赋,枝蔚如野道人,本无意于蓬莱,间一翻及经卷,送日而已。筐中偶携《黄山谷集》,见有《拟省题四首》,试和其二,聊资游戏;此外二题,非志所存,亦懒及焉。”且不论其所和《岁寒知松柏》、《被褐怀珠玉》二题所隐含的诗人的微妙心态,但就其待试期间仍携《山谷集》研读,又和山谷诗,已足以看出溉堂对宋诗的态度。
应如何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呢?其实,只要我们通读溉堂一生诗作,便不难发现,溉堂诗取径甚宽,不主一人一家。先就其诗题来看,即有《薤露行仿子建》、《饮酒二十首和陶韵》、《短歌行拟王建》、《田家杂兴次储光羲韵》、《劝酒效乐天》、《不如饮美酒效乐天体》等等。另外,王士祯评溉堂诗又云:“古诗能发源十九首、汉魏乐府,而兼有陶、储之体,以少陵为尾间者,今惟焦获先生一人耳。”[4]施闰章也说:“其诗操秦声,出人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5]汪揖还说:“甲申诸律气格绝似刘诚意。”[6]通过这个简单的排列,我们即可知溉堂诗自汉魏古诗到唐宋明诸大家之作均有效仿.而这种创作实践与其诗学主张又是完全一致的。溉堂曾在《叶思庵龙性堂诗序》中间接地谈过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说:余谓林子羽与高廷礼,亦自闺中健者,独惜其诗但从唐人入耳。[7]慨堂为林鸿、高揉作诗只学唐人而惋惜,可见在他看来诗学的路径一定要宽.他在《论诗》绝句及其注中,还进一步公开自己的诗学旨趣。溉堂道:“论诗不见安石公,风韵天然谁解夸。纸作牡丹工剪刻,何如阶下刺桐花.”注日:“安石公著《颐山诗话》,尝与杨用修论诗,谓论诗如品花,牡丹、芍药,下逮苦栋、刺桐,皆天然一种风韵。今之学杜者,纸牡丹、芍药耳。”溉堂主张诗国百花竞放,因此他学诗也就不主一家一人,而是博采众长,熔铸出自己独具的诗风来.
溉堂诗风多变化,每一时期的创作风格都不尽一致。而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在《溉堂前集》、《溉堂续集》和《溉堂余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大致来说,《前集》、《续集》和《后集》分别代表了溉堂前、中、晚三个不同时期诗风的倾向,明显的印象是:前期学汉魏唐,但流于粗率;中期学宋,渐趋朴淡平安;晚期则自出己意,独具风致,以真率朴实为旨归。魏禧在《溉堂续集序》中曾准确地揭示过这个变化的过程。
三厚孙豹人先生,以诗文名天下垂三十年。余往见《溉堂初集》,古诗非汉魏、律非盛中唐则不作,作则必有古人为之先驱。……已酉八月,余客南州,豹人别且八年,忽自楚中至,其颜涯丹,其锐髯洁白如雪。相见执手劳问,既出其《溉堂续集》示予,予袖而藏之。……予归客馆,雨大下,烧烛发袖中诗读之,乃渭然而叹曰:甚矣,豹人之能变也!今其诗,自宋以下则皆有之矣。冲口而出,摇笔而书,磅礴奥衍,不可窥测。
魏禧所揭示的虽然只是溉堂诗《前集》与《后集》之间的变化情况,但对我们全面认识溉堂诗风却很有启发。此外,李天馥在《溉堂诗集序》中又说:“豹人之为诗,当竟陵、会亭互相兴废之际,而又有两端杂出旁启径窦如虞山者,而豹人终不之顾。则以豹人之为诗固自为诗者也.夫自为其诗,则虽唐宋元明昭然分画,犹不足为之转移,况区区华亭、竟陵之间!”李天馥指出溉堂为诗,不受时俗干挠,自脱依傍,实际上仍是称扬溉堂诗取径之宽。而邓之诚先生称:“其诗由苏以学杜,[8],显然不确。
溉堂诗在《后集》中,则渐趋老成,渐臻佳境,质朴的风致愈加突出。给《溉堂后集》作“序”的王泽弘和方象瑛,作为溉堂的诗友,均已明确指出过这一特点。王《序》道:“余闻海内诸君子论诗者云,豹人先生得力在一u2018朴u2019字.”方《序》亦言:“……一因得读别后诸诗。大略数卷中岁不多作,而古健质直,旨趣遥深。”尽管由于溉堂学宋,曾使时人“大非之”,但他学宋,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质朴的诗风,是在变化出自己的性情面貌.而溉堂正是以其质直纯朴的诗风最终燕得了清初诗家的普遍肯定与赞誉.汪懋麟《溉堂文集序》云:
予论诗,于当代推一人,为征君孙豹人先生。其为诗,不仅宗一代一人,故能独为一代之诗,亦遂为一代之人.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溉堂诗,理应在清初诗坛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溉堂虽居广陵,然而,“秦风”的沾溉却丝毫不见衰减。其质朴而略显粗率的诗风,又何尝不是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创作的总体风致?
和焦获寓楼
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年间第一个己酉年)夏五月,潜江县城衙门前正街,建起了一座西向的新楼。
这是知县王又旦为迎接故友、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盖的住所。孙枝蔚客游四方,他受王又旦之邀,来潜江采风问俗。这次是从丰城出发,在汉口逗留数日后,“便往潜江”的。王又旦工诗善书,嗜友若渴,为孙枝蔚的寓所亲笔题写了“焦获寓楼”的匾额,安排好他的食宿。孙枝蔚旅途不乏艰险之事,但是在这个多雨的汛期,踏上当年地势低洼潮湿的潜江,他感受到的却是水患的无情。绵延的大雨使江河泛滥,冲溃了堤防。他目睹涨水的汉江和大水淹没的村居,写下了充满忧虑和同情的诗歌:“我行历四方,对此但哽咽。”他同时也牵挂着在堤上奔走救灾的知县王又旦,看到友人“行堤视水,归来益瘦甚”,多次写诗宽慰,并赞誉其为“贤令”。孙枝蔚此行,还带来了布衣诗人吴嘉纪(字宾贤,号野人)的新诗稿,他评点后,又因为“美玉难攻,虽欲效他山之石不可得也”,想想“知味赏音”的不会只是王又旦一人,便“携向潜江”。诚如孙枝蔚所料,雨水并不能阻止慕名来访者的脚步。孙枝蔚下榻的焦获寓楼,常常响起潜江“佳士”的敲门声。他们谈论起学问来,十分投机,不分早晚昏晨。频频和孙枝蔚唱和诗歌的潜江人,有志称“经学家”的贡士朱士尊(字伟臣,一字石户)、进士莫与先(字大岸),还有刘声玉等。“异县往来谁最密,朱家出去到刘家”。在朱士尊的编柳草堂,他们一起饮酒谈诗。朱士尊的儿子朱含晖(朱载震之弟,莫大岸之婿)和刘声玉的儿子也来做陪。在城南明末崇祯贡生郭铗的谩园,潜江的文朋诗友们,也为孙枝蔚举行过一次宴集。孙枝蔚和朱士尊、莫大岸等人都留下了《谩园宴集》的同题诗歌。谩园主人郭铗,则对如上三人的诗分别作了《次韵奉和》的赠答诗。可见当时十分融洽而热烈的气氛。在谩园梅花亭,虽非梅花开放的季节,孙枝蔚却热情洋溢地留下了二十一联的长诗《梅花亭子歌》。虽然“今年五月客潜江,绕郭洪涛碍杖屦”,但水退之后,郭铗“三日两日勤相邀”,得以欢聚。孙枝蔚以诗寄情,表达了在潜江的另一番感受:“潜江之行颇不恶,潜江高士复可慕。”潜江段天门(本名陡云,字郇五),以布衣吟诗,默默无闻,孙枝蔚读其诗后,大为推崇,人始知其工诗。孙枝蔚旅居潜江三月之久,创作了不少堪称诗史之作的诗歌。《潜江明清诗选》收录其旅潜诗作21首,居该书外地作者选诗篇数之首。在其著作《溉堂集》中,还有另外二十余首相关旅潜诗作。他的《焦获寓楼杂诗》(八首),因写的情真意切,古朴淡雅,深受当时一些著名诗人极力推崇。诗中可见孙枝蔚当年在寓所的活动和情怀:“仙人爱楼居,而况老腐儒,楼居有何好,可以读我书。”他曾经希望“不买千间厦,亦建三层楼”,目的是“厦以庇寒士,楼以望神州”。公则胸怀天下寒士,私则满足观光雅兴。但“此志今已矣,三叹不能休。”诗人“做客厌朝眠”,起得很早,却故意说“楼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风势拔屋,梁尘坠满案”,他担心酷爱的书籍被吹乱了,“呼童急收书,已愁缃帙乱”。但诗人更关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时江湖里,危舟谁相看”。体现出诗人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寓楼非真宅,不久须远别”。三个月后,孙枝蔚离开了潜江。在给王又旦的多封书信中,他表达了对潜江友人的思念之情:“甚思再游潜江久矣,潜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莫(大岸)如朱(士尊)如刘(声玉)如郭(铗),乌得不思?”“仙人爱楼居,而况老腐儒,楼居有何好,可以读我书。”他曾经希望“不买千间厦,亦建三层楼”,目的是“厦以庇寒士,楼以望神州”。公则胸怀天下寒士,私则满足观光雅兴。但“此志今已矣,三叹不能休。”诗人“做客厌朝眠”,起得很早,却故意说“楼高天易曙”。有一次“怪风势拔屋,梁尘坠满案”,他担心酷爱的书籍被吹乱了,“呼童急收书,已愁缃帙乱”。但诗人更关心江湖中的危舟:“此时江湖里,危舟谁相看”。体现出诗人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
是不是明代遗民
溉堂因被迫参加了康熙十八年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因此,后世多将其排除于遗民行列.卓尔堪《明遗民诗》不录溉堂一诗,绝非漏收;现存各种《明遗民录》中,都没有溉堂的名字;钱仲联先生主编之《清诗纪事》,在《明遗民卷》中亦不见溉堂之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很有必要为溉堂一辩。康熙十七年诏开的博学鸿词科,一直到第二年3月l日才开科考试。一时间,四方硕儒名士云集京城,其中有屡辞不获准而勉强应征的,也有自愿应考者。孙枝蔚显系前者.当时,陕西举荐者凡9人,李顺托辞有病、以死相抗,未至京城;王弘撰虽至京,但亦托病拒上考场;其余7人,孙枝蔚、李因笃、李念慈、李大椿、王孙蔚、程必升、赵廷用均上了考场,但结果除李因笃一人中式、孙枝蔚赐衔外,其余5人均告落第.李因笃似乎很不幸,他名声太大,荐举者多,当局必欲致之”母亲也“劝之行”,推辞不过,“涕泣就道”。结果金榜有名,却不愿出仕,不得不以一份情词恳恻的《告终养疏》来请求放归,很像是下了水又赶忙往岸上爬.然而,遗民的资格就这样丢了,并且还遭到友人的谴责(亭林于《答李子德》中不仅说:“愿老弟自今以往,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则所以全之者大矣”;而且道:“窃谓足下身摄青云,当为保全故交之计,而必援之使同乎已,非败其晚节,则必夭其天矣。”)甚至连沈德潜也说:“圣主之仁,人子之孝,字同共称”,显然微含讽意。当然,读《受祺堂诗文集》,我们又的确感受到李因笃的内心时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痛隐之中。
孙枝蔚的情况更特殊.被荐应博学鸿词试时,他在扬州(豹人老友杜F闻说豹人被荐,曾有《与孙豹人书》劝其。勿作两截人,,见《变雅堂文集》卷四),并且已59岁了.屡辞不允,勉强进京,不得已进了考场,但又“不终幅而出”,也就是说试卷未答完即出了考场.
诗词茶人孙枝蔚
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今西安市)人,长年寓居江都,生卒年不详。
他的家庭世为商贾,明末兵荒马乱,他拿过刀枪打过仗,后脱身到广陵重操祖业,纵横商海颇为得意。扬州在清初为人文荟萃之地,这使他决心执笔从文,于是闭户读书,间而为诗,从此以诗文垂名文坛30年。由于其出身不是官宦世家及书香门第,因而其诗常“快所欲言”,“岸然自得”。
孙枝蔚弃商后断了生活来源:“家渐落,诗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环堵萧然,左对孺人,右抱稚子,长年刺促乞食于江湖间”。(间或为幕府宾客)。他极嗜茶,而诗中绝不掩饰贫穷。有一诗中说:“馀生又断功名分,谁赐头纲八饼茶?”另诗又说:“妻儿乞米向谁家?高贤受饿也寻常……平生不识孟谏议(指卢仝茶歌典故),何人为寄月团茶?”久居殊方初病渴,每煎佳茗似逢医。”“虎丘三月曾停舫,惠水他时喜满铛。安得长谐住山愿,与君亲手采兼烹。”
茶肆、茶坊、寺院是孙枝蔚饮茶常往之地。《题茶坊…》诗中说:“缓步江头日未斜。来尝野店雨前茶。”“不待千金能一笑,诗人只有买茶钱。”其《客句容五歌》诗中,更是说得惨极:“可惜囊中无一钱,忍渴空过茶肆前。”
诗句中的“忍渴”,并非仅其本意。如果只为解渴,喝一杯水也可解决。“忍渴”有其广义,便是他在另一诗中所说:“知我性癖耽书籍”。“邀过茶肆每清谈。”茶肆里虽然人稠众广,但仍是知已的穷文人可以纵论读书心得,促膝相谈一切甜酸苦辣的宝地。其又一诗中也说:“淹留竟日惟茶话,第五名泉近可供。”虽未标明是否在茶肆里,但在茶话的时间夸度上达到“淹留竟日”,也是极为畅意了。
寺僧多为孙枝蔚的茶友,他在另一首咏第五泉的诗中说到“山僧泉上逢”时,便说“客来惟汲水,茶罢欲鸣钟。”结尾又说:“听经吾未得,涧边愧长松。”声明他不是听经人,只是沉浸于茶话而已。
孙枝蔚对生活的困境并不感到难受,而且觉得自傲。他的诗句说:“何以润我喉?新茗似头网”。(这里的润喉,与前面的解渴,其意相同)。他在“自焙临泉茗,闲赊隔舍醪。”中,还豪气横溢地自夸自赞:“中宵云共榻,五月雪明袍。”虽然穷,但还是与云共榻,以雪明袍。其才思之雅,气势之大,无以复加。在《客中苦热……》一诗里,他说:“野翁诗数卷,气与冰雪同,急归且把读,煮茶听松风。”在饮茶中,并细读“气与冰雪同”的友人诗卷,就能达到防暑降温。这诗的末尾,他又升华到高耸入云的精神境界:“何必??嵛顶,赤脚拄青筇。”更使人叹绝。
有一次,他与好友到“江深阁”的茶肆里饮茶,写诗道:“看花但恨眼初昏,且把茶经共讨论,传语江神须庆幸、久无渴梦不思吞。”“江深阁”茶肆似在江畔不远。孙枝蔚气吞扬子江的气魄多么巨大,多么惊人,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其诗:“多激壮之词,大抵如昔人评苏轼词: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
孙枝蔚所写茶诗茶词,落笔时文思连翩,常能与各种客观实际结合,这是他比其他骚客、茶人略胜一筹之处。例如他的《采桑子(题焦山僧房)》一词道:“老僧头白焦山顶,不菅兴亡,安稳禅床,卧对江南古战场。客来坐久深无语,饭熟茶香,归路茫茫,水打空船月照廊。”此词是从“饭熟茶香”中引出的对国家兴亡之感,词末有另二词人评语,一为“凄凉满纸”。一为“有伯符(东吴开国者孙策)当年气概。”又有一次孙枝蔚给一个当官的茶友写诗中说:“牛忙春雨后,犬懒月明中,治下多贤士,谁为桑苎翁?”这是他将茶圣陆羽的勤奋钻研精神与为民勤政挂起了钩。还有一首诗把咏茶与送友归葬其母联系起来。笔者多年来搜集茶诗成千上万,
如此茶诗却是第一次见到。诗中说:“昔时茶叶肥,常得高堂夸。茶树今在眼,茶味也不差。儿归母不归,虽归如天涯。”诗句朴实无华,读之使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