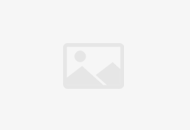潘旭澜的个人简介
潘旭澜,男,1932年11月出生,2006年7月1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逝,汉族,福建南安人。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9年兼任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先后被选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简介
潘旭澜,男,1932年11月出生,2006年7月1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逝,汉族,福建南安人。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履历
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兼任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先后被选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问。
作品
著有《艺术断想》、《潘旭澜文学评论选》、《长河飞沫》、《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太平杂说》、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十年文流》、《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等获国内外20多项奖。近二十年来,潘旭澜先后获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文教机构的学术、教育、创作奖二十余项。传略被收入国内外几十种辞典、书籍。《太平杂说》在史学界影响很大,是一部不多见的优秀作品。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走了,去往了 另一个世界。――这天,是2006年7月1日。这些天里,陆续读到一些悼念潘老师的文章。我知道,还有一些悼念潘老师的文章即将发表;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正在写或将要写类似的文章。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公开发表一点悼念潘老师的文字。但这些天来,大脑时而如冰结的湖面,挤不出半句话;进而又似杂草丛生、百物喧闹的池塘,理不出一点头绪。于是便想,等心情平静后再慢慢写吧。然而,《随笔》的麦蝉女士来电话,说《随笔》想在第五期发表一篇纪念潘先生的文章,已留好版面,并命我来写。又说,潘先生是《随笔》多年作者,读者也期待着尽快在《随笔》上看到悼念潘先生的文字。《随笔》是潘老师生前极推重的杂志,多次对我说过,要重视《随笔》,并希望我也成为《随笔》经常性的作者。潘老师病逝,《随笔》送了很大的花蓝,还发来了唁电。在众多唁电中,《随笔》的唁电因既朴实无华又情真意切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随笔》命我赶写一篇纪念潘老师的文章,我哪里有推辞的余地。
中国有一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我看来,这应该是父子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这必须是父子关系在多年间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变为兄弟般的关系的。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两代人之间没有代沟,没有价值观念上的重大分歧;意味着两代人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意味着两代人之间有着那种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和心照不宣。但在中国,这样的终于成了“兄弟”的父子,其实历来是不多的。虽说中国还有一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潘老师与我,毕竟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子。所以,我虽然极想用“多年父子成兄弟”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但终于觉得不妥。我又想用“多年师生成兄弟”来表达心中的感受。如果真这样,我觉得潘老师未必会怎样见怪,极有可能是在略显惊讶之余,以淡淡的苦笑来默认这种放肆。但这对许多活着的人,是大不敬了,终于不敢。人的一生,会与许多人相遇、认识、交往。但真正重要的人却并不多,无非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这样的人一旦离去,你生命中的某一部分也就被他带走了。潘老师离去后,我几次想对老师的女儿潘向黎说,我失去的,也许并不比你少。――但也终于没有说出口。
成为潘老师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1978年,我以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我记得,那年填志愿可填十所院校,五所重点院校五所普通院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此外一项就是“是否服从分配”。那时的人,能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都是天大的幸事,当然填“服从”。何况,如果“不服从分配”,此后几年内就“不准报考”。但后来,所有的志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服从”二字起了作用:先期介入录取的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那时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什么,我不清楚),在安徽录取十名文科学生,我竟被他们的“法眼”看中。少年时的我,也曾有过一些梦想吧,但我即便是发高烧时,也没敢想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入学的同时穿上了军装,我从未感到过威武,只觉得别扭。在校期间,虽然外语学得很刻苦,但常常是“瞻望前程,不寒而栗”。我“栗”得并不多余:1982年7月,我被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接进了大别山中。那时我虽然尚不满二十岁,但却常做被活埋的梦。幸好,不到一年,单位就搬到了南京市。南京当然比山沟要好些,但心情仍然是极为苦闷的。那几年,我年年打报告要求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但年年被驳回,且屡遭主其事者的嘲讽、挖苦。1985年12月(或者1986年1月)的一天,《解放军报》上登出了总政治部关于现役军人报告研究生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现役军人可以报考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生”。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低头把这句话看一遍,抬头想一想;低头看一遍,又抬头想一想。这样地看了三遍想了三遍后,一转身去了干部科。这回他们无话可说,同意我报考地方院校了,并且说好,一旦被录取,即办理转业手续。报名时,我未多考虑,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潘旭澜老师。当时,一些善意的同事,曾劝我报考差一些的院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好不容易等来了这样一个机会,应该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的院校。但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后来我一直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因为报名刚结束,总政治部新的规定就下来了。大意是,本年度已经报考地方研究生者,允许他们参加考试,但考取后不得转业,毕业后仍回部队工作;以后现役军人则仍不得报考地方。新的规定,又让我体验到什么叫“背水一战”。
但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意识到命运出现了转机,虽然不能转业将高兴大大地打了折扣。1986年9月,我正式成为潘老师的学生。入学后,潘老师几次对我说,是否录取我,他“考虑了一星期”,原因则在于我的试卷字迹太潦草。我在后怕之余,又有些不解。我平时写字,的确是非常潦草的,而且潦草得毫无章法,完全是一套自创的“文功”。如果是写文章,那草稿就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过些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看不懂。我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在答卷时是有意识地克服了的。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我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将字写得工整了。饶是如此,还是差点因字迹潦草而折戟沉沙。后来,当我较多地体味到潘老师做人做事的认真后,我就不以他那“考虑一星期”为怪了。就说写字吧,他除了偶尔有一些笔画十分合乎章法地带点行书的写法,基本上是一笔一画地写。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就是写一张最无妨随便的便条,也是那么清清楚楚、一丝不苟。我从没见过第二个人如此认真地对待写字。我有时想,如果他正在那里写一张便条,你告诉他房子快要倒了,他也仍会横是横、竖是竖地把字写完。当然不只是对待写字才如此认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写篇文章不容易。”所谓“不容易”,也就是认真得近乎不近人情。他从不会有了一点想法就写,总是要反复考虑、反复掂量。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那种灵机一动之作,总是在脑子里放了很久,少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几十年。写完后看看、改改,改改、看看,是自不待言的了。写完后整体性地不满意,觉得没有把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而推倒重来,也决非罕见。几番重写后仍不满意,他就会把这题目暂时放下。从潘老师那里,我悟到一个道理,即人们对待自己的文章,是有着两种心态的。一种把读者的反应放在第一位,能博得读者叫好,就好。至于文章是否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则在其次;更有甚者,为了换取读者的喝彩,不惜说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见。只要看看有些人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就知道他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玩笑而已。另一种当然也考虑读者的反应,但是否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否把想说的话说清楚了,则永远被置于首位。潘老师是后一类的典型代表。浮而不实、哗众取宠,从来与他无缘。
潘老师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辞典》,以其全面和准确、以其尊重事实的勇气、以其考察“新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而受到广泛的称誉。潘老师去世后,我曾在他书房里随便翻书。一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寄赠的专著,扉页上写着“您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辞典》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巨大帮助。”我知道,这位学者与潘老师平素并无来往,他也实在没有必要对潘老师曲意奉承,所以这决非客套。这部《新中国文学辞典》之所以成为精品,就因为潘老师异乎寻常地认真。在那个漫长的编写过程中,他不知道生过多少气,发过多少脾气。他多次对我说,为编这部辞典,“至少少活五年”。应该说,当年参加编写的人,谁都不曾马虎过。但你的“不马虎”与他的“认真”之间,实在往往有一段距离,这就难免“挨骂”,难免返工。――有许多词条,是经过多次返工的。在他写作“太平杂说”的日子里,书房里连地板上都堆满了各种史料,每一本里都或多或少地夹着纸条。“太平杂说”采取的是学术随笔的方式,一般不做注释。但却是无一句无来历的。他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史实方面的质疑的。“太平杂说”大都数千字一篇。但每写一篇这样的“杂说”,他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正因为他在论述史实时的严谨,后来的质疑倒并不在史料方面。――一位中文系的教授写出的这样一本书,竟然没有哪位史学专家在史料上提出疑问,即便恨得牙痒痒,也只能在“观念”上说一些业已说了一辈子的话,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潘老师认真,但却并不迂腐、呆板和固执。写字工整易认,是他长期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当电脑开始流行,有人开始用电脑写作时,有一天他颇为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可以用电脑写作了,写字不再成为问题。我以后对别人的写字没有要求。”我明白,这是在写字一事上为我“松绑”。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不少人认为潘老师脾气倔,容易生气。应该说,潘老师性情中狷介的一面确实比较突出。刚投到潘老师门下的那几年,见到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制怒”二字。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这也说明他在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这方面的性格。我以为,潘老师性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刚成年便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的。从家乡闽南到上海,与其说是求学,毋宁说是求生。虽然留校任教,也仍然因为“家庭问题”受到歧视,被固定在“助教”的职位22年之久。“文革”十年,更是饱受摧残,完全可以说是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婚后多年分居,他只身在上海打熬,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苦撑。“文革”结束,他也人到中年了。直到这时,师母和孩子才到了上海,他才结束了几十年的单身生活。我刚到复旦那几年,在与我交谈时,他多次说到,自己是没有青年的。他的意思是说,从未体会过青春的健康、浪漫、欢乐,从未有过青年时期的无忧无虑、轻松愉快。每当说到这些,语气里总充满遗憾。正因为自己的人生如此残缺,他特别希望我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固然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虚度时光,但也常常强调,即便是一个学者,也不应该“成为读书写文章的机器”。我在读博士期间,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晚上总是睡得很晚。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便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年轻时不可太熬夜,身体上的透支是要加倍付出代价的。――他不知道,我每天上午的懒觉也睡到很晚,睡眠时间只比别人多决不比别人少。晚睡只是一种习惯,决非刻意透支身体。他大概觉得我是很用功的吧,后来就常常对我说,不要总在那里读书写东西,有时也和同学出去喝喝酒。――他不知道,我不但常常和同学出去喝酒,更常常一个人在宿舍喝酒,地上胡乱放着的酒瓶总令来访者一进门便一声惊呼。
半生苦难,使潘老师性情中有了较为易怒的一面。身心上的苦难,倒还在其次。学术生命的长期中断和不可弥补,是令他常常烦躁的主要原因。潘老师留校任教后,便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势头,是那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才俊。“文革”使他起步未久的学术生涯中断,更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健康,使得后来想“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也缺乏身体上的本钱。他曾对我说,“文革”前他已完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稿。“文革”开始后,他将书稿藏在一亲友处。“文革”结束后,他想取回,却得知书稿已在“文革”中丢失。他说,这件事令他“好几年不痛快”。而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分明感到他并未完全释然。这件事我只听他说过一次,此后再未言及。这分明是他心上的一道伤口,他不愿多碰。大概是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在他家中,他对我发了火,火势并不大。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他的火发完,两人便无言地僵坐着。过了一会,师母招呼吃饭。于是留下来吃饭。我那时能吃且贪吃。在餐桌上坐下,便毫不客气地饕餮起来。桌上的一只鸭子有一半入了我的腹中。几天后,在一个路口与他相遇。他走过来,站住,板着脸,说:“那天因为心情不好,你不要介意。”说完扭头就走,把我扔在那里发呆。后来我知道,那天在我走后,师母责怪了他。他显然接受了师母的批评,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一个学生道歉。
但这种发火的事却并不多。从硕士到博士六年间,我所遭遇的也只有那么一两次。从他那里,我更多地体会到的,是宽容。我觉得,他实在比许多貌似平和温厚者,要宽容得多。像我这样一个不拘小节、毛病多多的人,能为他所喜爱,前提是他宽容了我身上那些他并不喜爱的东西。――而这是那些貌似平和温厚者往往难以做到的。与其说他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毋宁说他是一个有性情的人。回首复旦的六年,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他对我的宽容。现在的研究生,要上许多课,已经本科化了。那时在复旦读研究生,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从硕士到博士的六年间,我几乎没有进过教室。潘老师在这些方面并不做什么要求。不但在上课上不对我有任何要求,在读书做学问上也从未有任何具体的要求。他采取的是任我自由发展的方式。而他的“指导”,都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在那一次次漫长的聊天中,他以甚至不让我觉察的方式,实现着对我的指导。当然,他自己也未必总意识到是在对一个学生进行指导。他只是在谈着他的人生经验,谈着他治学上的各种感悟,谈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书。复旦的一些老先生,是他常谈的话题。在他的书房里,我一次次领略到周谷城、刘大杰、朱东润等先生的风采。谈的最多的,则是他最为感激的鲍正鹄先生。1996年,潘老师发表了《若对青山谈世事――怀念朱东润先生》一文,这真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散文。文中所写到的事,我不止一次听潘老师讲过,但我仍然被文章所感动。当然,潘老师对我讲述的朱先生,比他所写的要更丰富。有些事他并没有写。对这些老先生,潘老师在聊天中当然更多的是赞赏。但也偶有非议。他多次对鲍正鹄先生的博雅精深赞不绝口。鲍先生前几年辞世,潘老师写了《漫天飞雪――送鲍正鹄老师》一文,其中说到“一位上世纪80年代至今极有声名而且绝不随和的学者,送书给鲍先生,总称之为通人、方家。”这位学者,就是钱钟书先生。然而,他也多次对我分析鲍正鹄先生在个人著述上成就甚少的原因。除了一生为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缠身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眼界太高。因为自己太有学问,鲍先生对同时代的学者大都不太恭维;对自己写的东西,也总不满意。因为写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东西,就干脆不写。对这一点,潘老师显然是并不苟同的。他说,对人对己,都不应该求全责备。对人求全责备,世间便无可读之文;对己求全责备,就会终身一事无成。
这样的谈话,让我深切地体验到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样的谈话也很快让我上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总是在晚饭后并无预约的情况下敲开老师的家门。我那时的想法是,如果老师有急着要做的事,我稍坐片刻便告辞。但稍坐片刻的事一次也不曾有过。总是从晚上七点来钟谈到午夜。总是在谈兴正浓时忽觉夜已很深才戛然而止。现在想来,当然不是他从不曾有过急着要做的事,而是有再急的事,他都放下了。“无知者无畏”这说法是有几分道理的。那时的我比现在更加无知,因而也更加放言无忌。在与潘老师的交谈中,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无理的话、荒谬的话,不知道多少次口出狂言、妄下雌黄,但都他被视作是一个年轻人可以原谅的毛病、或被视作是一个人可以原谅的个性而予以宽容了。那时复旦有硕士生可提前一学期攻博的制度,手续极简单。硕士读到两年半时,有一天潘老师把我找去,说准备让我提前攻博,问我是否愿意。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愿意!”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潘老师带着我到了贾植芳先生家,贾先生问了我几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就算是通过了面试。新学期一开始,我就把铺盖书籍搬到了条件好得多的博士生楼。与潘老师的交谈,也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了。开始的几年,谈的主要是学术问题和一般性的人生问题,后来则向政治方面拓展,谈起了“莫谈国事”的“国事”。一些如果不是对一个人彻底信任便决不会说的话,也开始从嘴里缓缓地流出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些令人紧张、焦灼的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向他说说外面的情况,一方面也是听听他对时局的分析。有时我在外面活动到很晚,也仍然要敲开他的家门。我本来应该是在1991年底毕业的。其时复旦中文系已决定我留校。无奈军籍在身。要获得军方的同意,难如上青天。为争取时间与部队交涉,我以论文未完成为由,延长了一学期。拖到了1992年夏季,军方的绿灯仍然没有亮起,我只得离开复旦,回到了南京。
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交谈仍然继续。每次到上海,无论有别的什么事,我都是先直奔复旦,在招待所登记好房间,立即去他那里报到。聊天总是从下午二三点钟开始,到吃晚饭时分,他必定到附近饭馆请吃饭,且必定喝酒。吃完饭回到书房继续聊。到夜间十时左右,他必定拿出好几种点心和好几种酒。就这样喝着、吃着、聊着。谈的虽然也无非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非是文学、文化、学术,但说的往往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常常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夜深时分,如果潘老师的小女儿潘向蓁在家,必定推开门,问是否需要烧点东西吃吃。晚饭已经酒足饭饱,且又在不停地喝着、吃着,实在不需要。所以我开始总是辞谢。再过一会,她又推开了门,把刚才的话又问一遍,我仍然辞谢。她带上门时,脸色已有些不好看了。几分钟后,门又被她推开,这回语气和问话都不同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吃,还是不吃?”再要辞谢,那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是连声说:“吃!吃!吃!”不一会就会有两小碗热气腾腾的夜宵端进来,精美而可口。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聊天,更多地是通过电话。就像当年过一段时间就想去敲开他的门一样,离开上海后,过一段一时间就想拨通他书房的电话。他也常常打过来。通常,他总是在夜间喝得微醺时,拿起电话找我聊天。无论是我打过去还是他打过来,都跟见面时一样,要聊到深夜。我从去年春到今年春,在日本一年,即便这期间,这种电话中的长谈也没有中断。电话交谈与书房里的促膝谈心毕竟不同。在谈到“莫谈国事”的“国事”时,其中的“关键词”常用代号,双方并没有任何约定,但却一说就懂。对“国事”,潘老师有着深切的关注,也常有精彩的分析。他闲谈中对“国事”的议论,常让我想到当年《大公报》上的社评和“星期论文”,让我想到张季鸾的《南征北伐可以己矣》、想到胡适的《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想到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只是如今没有《大公报》,他的这些看法,只能作为“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对我这个学生发表。
去年三月中旬,我赴日本前去了一趟上海,算是去向他辞行。仍然是从下午谈到深夜,仍然是他迈着因喝酒稍多而略显踉跄的脚步把我送出小区,仍然是希望我多住几天。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在招待所房间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他忽然推门进来了。我稍稍有些惊讶。因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在沙发上坐下,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说:“抽支烟再走。”我于是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两人隔着茶几,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烟,他站起身,说:“走吧,晚了赶不上车。”于是一同出门,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直到把我送上车,他才转身回去。今年三月底,我从日本回来。一回来便杂身缠身,只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原想暑假去上海,也准备了一肚子的日本观感要对他说。然而,五月初便得到他住院的消息。再见他时是在病房里。当医生表示回天无力时,我才悟到,去年三月我去上海,其实是最后一次与他促膝长谈。而他莫非冥冥中有什么预感,才有那多少有些反常的行为?二十年间,与潘老师的交谈,是我生活中一份特别的快乐,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因为这种交谈从学生时代一直继续下来,我便始终没有找到“毕业”的感觉。现在他走了,也把我的这份快乐和享受带走了。而我,也真的“毕业”了。
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越不知如何说他。关于潘老师,我可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我觉得,最不应该忘记说的,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思想文化界的一道金色的风景。这群老人,人生经历各各不同,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也曾差别甚大。但在步入老年时,他们却在精神上走到了一起。促使他们站到同一精神立场的,首先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这种“人间情怀”又使他们坚信人类的共同价值。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文字方式,呼吁着、抗争着,执着地表达对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追求。在别人含饴弄孙的时候,他们艰难地担当起启蒙者的使命。他们与知识文化界那类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领头羊”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知识文化界那类“过于聪明”的人形同水火。某种意义上,不妨说这是一群过于呆傻的人。但这群老人,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宝贵财富。潘旭澜老师是这群老人中的一员。步入老年后,潘老师在精神上给人以强烈的越活越年轻的感觉。退休后,他本来有许多写作计划。有些题目已准备得很充分。例如,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对《儒林外史》情有独钟,早想写一部《吴敬梓评传》,这方面的资料他搜寻了几十年,早就不成问题了。再例如,他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有许多自己的看法,早想写一本《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主编《新中国文学辞典》,某种意义上是为撰写通论做准备。但他让心爱的吴敬梓靠后,也让《中国当代文学通论》靠边,先写起了“太平杂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太平军”的“杂说”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表达他对现实的关怀,或者说,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心”。当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现代教育家被普遍肯定时,他觉得不应该忘记罗家伦的贡献。因为罗家伦当过近十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南大百年校庆时,他多次来电话,询问我在校庆中是否提到了罗家伦,怎样评价了罗家伦,并嘱我代为搜集校庆中出现的有关罗家伦的资料。后来,他写了《〈玉门出塞〉及其他》一文,对罗家伦给予了公允的评价。这篇文章在广东的一家刊物发表后,罗家伦的女公子从美国来信,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因大陆开始公正地评价罗家伦而改变了对大陆的看法。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后,潘老师颇为义愤。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歌颂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写了《什么〈英雄〉》一文,对电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他住院期间,在他辞世前的那段日子里,他对自己的病不谈、不问。谈的、问的,仍是关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问题。在这期间,他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地赶到病床边。日本的小林二男教授(他曾在复旦进修)和安本实教授(他曾在大阪听过潘老师的课)闻讯也赶来了。他们并未约定,但都在6月16日这天下午来到了病床边。其时潘老师谈吐已很吃力了,说话断断续续,口齿也很不清楚,有人来看他,都要家人“翻译”。然而,这天,他对着日本的两位教授,字字清晰地问道:“现在日本有一种u2018中国威胁论u2019,你们这二位知华派怎么看?”我惊异于他忽然说话如此“正常”,更惊异于这位清楚地知道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老人还在关心这种问题。有一天,他正处于昏睡状态,鼾声大作。我与陪护的潘向黎的先生刘运辉坐在床边闲聊。为怕惊醒他,我们的声音都并不高。闲谈中,刘运辉说:“现在各地大学的u2018百年校庆u2019,闹得太过分了。”我说:“是呵,完全是劳民伤财,也是今天的u2018怪现状u2019之一。”这时他忽然大声说道:“这个u2018百年校庆u2019,是应该狠狠地批!”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仍然闭着,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鼾声骤停。话一落音,鼾声又接着响起。――这一刻,我感到了骄傲。我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了这样一位导师和被这样一位导师所选择而骄傲。
潘老师所置身其中的这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精英。这些年,这群老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像金色的叶片在一片接一片地凋零。在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都普遍在庸人化、犬儒化的今天,这些老人的离去,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份“人间情怀”,使潘老师在活得充实的同时,也活得痛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不容易活得开心。他曾对我说:“从世俗的角度看,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但要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如同生活在地狱里。”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这一辈子都是苦多乐少的。七十几年,不算怎样的高寿,却已经大大超过他年轻时的预期了。在准备潘老师的追悼会时,大厅正中的挽联,师母命我来做。我凑成这样一副:
这里苦着呢!熬到今天真不易,总在盼盛世;
那边好些吗?遇见故人且尽欢,毋须说太平。
潘老师走了。一双深切地关注着我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在读书做学问上,没有谁比他更对我知根知底,也就没有谁的关注比他更到位。这么些年,他每读到我什么文章,每收到我寄去的书,总要打个电话,谈谈他的看法。当然不只是我。他对所有的学生都深切地关注着。平时通电话时,他常常要介绍师兄弟们的情况。谁发表了什么文章,谁出了本新书,谁的职称解决了,谁住进了新房……我知道,这些,都足以令他喜形于色。从电话里就能听出,他一定又多喝了几杯。他还有一癖。每当有学生与他同一期刊物发表文章,他便分外高兴,称之为“同台表演”。如果学生文章的位置比他更显著更重要,他的高兴就成几何级数增长。有时在电话里说起这种事,我感觉到,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差一点就要手舞足蹈了。陈思和先生在《告别潘旭澜先生》一文中,说他“心地其实很天真”,这大概可做一种注脚。这么些年,如果说我还不至于过于怠惰,原因之一就是不愿意令他过于失望。现在,我就是发表了再令他满意的文章,出版了再令他满意的书,也等不来他的一个电话了。想到这一点,心里空了许多。感谢杨苡老人在得知我的导师去世后打来安慰的电话。她老人家说:“既然是老师嘛,那就应该多写点东西。”我明白,她老人家是在提醒我,对老师最好的纪念,是做出尽可能多的成绩。这也让我意识到,潘老师仍然在深切地关注着我,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
我仍然找不到偷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