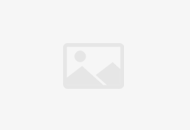舍斯托夫的个人简介
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二十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1866年出生于基辅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大商人。舍斯托夫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后来转学法律,于1889年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1895―1914年间居住在瑞士,但经常回国参加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宗教―哲学会议,投身于当时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流亡国外,主要居住在巴黎。在此期间他曾在大学任教,并撰写论著,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舍勒等,著名文学家布伯尔、纪德等交往,并在这种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中充实和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舍斯托夫 - 生平
舍斯托夫毕生的学术创作都集中于猛烈抨击传统形而上学和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十月革命之后,舍斯托夫被迫流亡巴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国流亡文化的杰出代表。“文化与流亡”携手并进,古已有之。但只有二十世纪的俄国哲人与诗人的流亡才成流亡文化史上最壮丽的一大景观,这一大批流亡的哲人中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基洛夫等,而尤以哲人舍斯托夫的言论最为孟浪激烈。与其他人相比,舍斯托夫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正由于此,他不仅受到来自思潮外部的尖锐批评,而且也受到别尔嘉耶夫等人的批评。不过,别尔嘉耶夫等在批评舍斯托夫的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的贡献,说他“以自己的全部存在进行哲学思考,对他来说,哲学不是学院专业,而是生死事业”。他的哲学“把认识过程同人的整个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存在的奥秘只有在人的生存中才能认识”。
1938年11月,正值他最重要的压卷之作《雅典与耶路撒冷》(Athensand jerusalem)问世之际,这位俄罗斯的儿子客死异乡巴黎。
哲学史家一般将舍斯托夫归类为存在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
舍斯托夫 - 思想简介
舍斯托夫认为,人的生存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人们要么求助于理性及其形而上学,要么听从为人们揩掉每一滴眼泪的上帝的呼告。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要沉重,爱才是生活的法则。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却被人们认为是荒谬和不可能的。
舍斯托夫坚决声称,正因为这种真理荒谬所以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才是肯定的。可是理性的人们至今对这种断言嗤之以鼻。所以舍斯托夫认识到,争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乃是一场疯狂的斗争-以眼泪、呻吟和诅咒以代价的斗争。按照圣经,这种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就是信仰。这种信仰的真理,对于这个世界的法则来说就是荒谬的。然而这种荒谬却最为可信。
“必然性”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至今多少哲学体系都以它为支撑点:基本原理以它为根据,体系之正确以它为前提,思想之力量以它为基础。在哲学领域中,人们都要追求合理性:就体系之外的事物而言,只有具备合理性才被承认有存在的权利;就体系之内而言,合理性又是能够具有说服力的基本原因。这也就决定了必然性地位之重要;必然性是合理性的内在根据,一个事物是否合理皆在于它是否包含必然性(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时,就是以是否具有必然性为根据来区分“现实”和“现存”的。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另外,必然性又是普遍性的全面支持,如果没有必然性,普遍性也根本立不起来,顶多只是外在的同一。这样,尊重必然性,甚至崇拜必然性,便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从古希腊哲学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莫不如此。
面对这样一堵“不听劝说”(亚里士多德语)的石墙,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竟敢用头去撞,这也是一个哲学奇观。
在舍斯托夫看来,被希腊哲学传统奉为真理之最后根据和道德之最后标准的必然性,并非那么神圣,因为所谓必然性实际上只是人对现实的一种认识和解释,而这种认识和解释又不过是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也就是说,必然性是人在无法改变现实时对现实的一种承认,一种顺从。这种承认和顺从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安慰,可以使人在失去自由时得到理论上的补偿。凡是在某种地方承认必然性,也就是在那里不再思考,不再深究,不再自由研究,也就是在那里做必然性的奴隶。这样看来,必然性不过是对现实的张目,因而它也就被统治者用来为自己的统治张目:必然性是坚不可摧的“石墙”,现实的政权既然具有必然性,所以它也是坚不可摧的“石墙”。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不能自己决定,他知道他的决定不在自己的掌管之下,他将走向必然性指给他的道路,习惯于‘内心平静地对待和忍受具有无上权力的命运带给他的一切’。全部哲学教导它们同样违背人的意愿,从探索真理变成了说教必然使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雅典和耶路撒冷》中译本,学林出版社,2000,118页)亚里士多德曾说,偶然性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无法把握,一个本想植树的人,可能在挖土时得到宝藏,也可能得到潘多拉匣子,这完全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必然性则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人们可以认识必然性,从而按照必然性行事,在现实中得到成功。舍斯托夫批评亚里士多德说,这样他就完全否认了人的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人既无法把握偶然性,只能做偶然性的奴隶;“既然是偶然性,科学与思维在此就无能为力,只应接受”(同上书,第304页);同时,人更无法支配必然性,只能顺从必然性,因为亚里士多德“深知‘必然性不听劝说’,既然必然性不听劝说又不可战胜,也许,就只能服从,无论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应当服从并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也就是必然停止。”(同上书,第4页)既然如此,人的自由何在呢?后来,斯宾诺莎干脆把必然性与自由混为一谈,声称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以后干什么呢?当然就是顺从。于是斯宾诺莎就进一步将人置于必然性的统治之下。这一思想被黑格尔从辩证法的高度加以肯定,使其罩上了灿烂的光环。甚至以宣扬“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闻名于世的尼采也在必然性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他在《看那这人??》中说道:“我衡量人之伟大的公式是amorfati(爱命运):不要改变从前、以后乃至永远的任何东西。不仅要忍受必然性,――更不要远避它,……而且要爱它。”舍斯托夫评论说:“他不想在任何东西、任何权威面前屈服,但当他一看见必然性之后,他的力量就失灵了:他给必然性建造了圣坛。”(同上书,第137页)
舍斯托夫尖锐地指出,给予必然性以如此崇高地位的哲学家们向人们隐瞒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必然性并不区别善与恶,它可能给人们造福,也可能使人们遭殃。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必然性所辩护的“现实”和“事实”带给人们的并非总是福音。舍斯托夫指出,必然性不管善恶,只管必然,只管对现实的“不可避免”的辩护,至于它的后果如何,它是不会过问也不会动心的。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点,以及它的强制性,所以当许多哲人将其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时,就不仅不顾其之善恶不分,只看重其之不可避免和强制,而且将对必然性的顺从看作最大的幸福。比如斯宾诺莎就是如此。斯氏曾说:他的学说的“效用在于教导我们如何应付命运中的事情,或者不在我们力量以内的事情。……直到使我们能够对命运中的幸与不幸皆持同样的心情去平静地对待和忍受”。(《伦理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第94―95页)舍斯托夫指出,在斯宾诺莎那里,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承认人的一切,它既不要欢笑,又不要悲哀,也不要诅咒,只需要斯宾诺莎称之为理解的那个东西”。(参阅《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第9页)在这种知识面前,人能怎么样呢?“日常经验或意识的直接现实是人们关于真理问题的最高审判级别:无论经验带给我们什么,无论‘现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接受,都把它叫做真理。在理性主宰的世界上,同‘现实’作对是明显的发疯。人能够哭,能够诅咒经验向他展现的真理,但他深知,要克服这些真理是谁也做不到的;应当接受它们。哲学则更进一步:‘现实’不仅应当接受,而且应当赞颂。”(《雅典与耶路撒冷》,第164页)舍斯托夫将这种态度概括为:“勿哭,勿笑,勿诅咒,只要理解。”
可见,必然性不仅不顾其带来的后果是善还是恶,而且其本身还被哲学家们推崇为最大的善。在此事上的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是他赋予了必然性以伦理意义,因为他将“善”与“知”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知就是善,“知识即美德”??舍斯托夫指出:“苏格拉底的无知并非无知,而是关于无知的知识,而且伴随着对知识的强烈的无可遏制的欲望,他把知识看作是逃避自己堕落后果的唯一途径。”(同上书,第155页);而知当然就是必然性的知识。这样,必然性就获得了伦理上的意义,“所有‘你应该’都同统治世界的必然有内部紧密的联系。因为它想成为无条件的??即像福音书中非受造的、摆脱了上帝的人。当必然宣布‘不可能’时,伦理就以‘你应该’予以协助。‘不可能’愈是绝对、不可战胜,‘应该’就愈是威严、毫不留情。”(《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第111页)后来的哲学家们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至用必然性吞没了人的自由。在历史哲学中这种理论更是占了上风:只要是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形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一律都是善的。至于人在这种社会形态和历史事件中,在这些历史人物的统治之下,究竟是得福还是受苦,那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历史只知道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有多少人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历史是不关心的。显然,这里存在一个谁来宣布事物、事件、现实、历史的必然性的问题。在这里,舍斯托夫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和权利正是被大人物(政治上的和学术上的)所宣扬的必然性所剥夺的。
根据舍斯托夫的思想,从根本上说,人的拯救也就是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问题。对此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自由不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因为人的自由是由人自己把握的,它体现为人的意志。如果意志受必然性制约,那么这种意志就是不自由的;其次,自由也不是对经验领域中的细微事情的决定能力,而是对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的抉择。他说:“人在经验领域是有某些自由的,但只是某些,相当于有限存在物所当有的那些自由。他可以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可以在几个相同对象中任选一个,甚至可以在更重要的场合只按照自己的偶然任性行事。但是,他面临的选择愈是至关重要,他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就丧失愈多:人注定不能决定选择善恶,不能决定自己的形而上学命运。当‘偶然性’把我们带向深渊,当多年的安宁无忧的生活之后突然像哈姆雷特那样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时,我们就开始觉得有某种新的、神秘的力量――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敌对的力量 ――引导着我们,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参阅《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本,211页)再次,自由也不是人在经验世界中进行善恶选择的能力。这种选择预先就已经将我们的自由限制在善与恶之间,而不能获得从世上根除恶的自由。舍斯托夫说:“既然要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已经丧失了自由:恶来到了尘世并开始与上帝的善并驾齐驱。”(《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第200页)
那么,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舍斯托夫说,那是一种“硕大无朋的、另一种性质的自由:不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使世界脱离恶”。(同上书??他以其宗教哲学为依据对此进行说明:“自由不在于选择善恶的可能性,如我们现在注定认为的那样。自由是不容许恶进入世界的权力和力量。最自由的存在物――神,不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神所创造的人也不选择,因为无可选择:天堂里没有恶。”(《雅典与耶路撒冷》,第170页)这就是说,人的自由是由上帝赋予的,这种自由使人与上帝一样成为全能的、幸福的,成为完全与恶无关的。但是,人类的祖先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知识树上的果子,这样,在他们能够知道善恶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他们被逐出天堂――伊甸园,开始了漫长的罪孽生活,也就是受必然性驱使的生活。人要想重新获得自由,就要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冲破必然性的牢笼,致力于彻底消除恶。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依靠信仰,用信仰战胜依赖于必然性的知识(因为知识总是告诉人们以必然性,让人们对必然性俯首贴耳)。这一根本性的任务也就决定了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的特点:“宗教哲学不是寻求永恒存在,不是寻求存在的不变结构和秩序,不是反思(Besinnung),也不是认识善恶之别??这种认识向受苦受难的人类许诺虚假骗人的安宁??。宗教哲学是在无比紧张的状态中诞生的,它通过对知识的排斥,通过信仰,克服了人在无拘无束的造物主意志面前的虚假恐惧??这种恐惧是诱惑者给我们的始祖造成的,并传达到了我们大家??。换言之,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圣的‘至善’。”(《雅典和耶路撒冷》,第22页)
这里表明了舍斯托夫对哲学的特殊看法,他认为过去的哲学万流归一,最后都成为一种说教,而这种说教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人们顺从必然性,理解“现实”,而不关心人间的痛苦和悲剧,也不能解决人类所遭遇的苦难。舍斯托夫要彻底改造哲学,这种改造就从对哲学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开始:哲学不应再是对人的说教,而应是为了消除人类的苦难,它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类最终战胜恶,回归上帝,重新获得上帝所赋予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至善”。
显然,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也是神秘主义的。在理论上,他将信仰与理性绝对对立起来,将必然与自由绝对对立起来,并将人类美好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上帝身上,寄托在回归伊甸园的神秘乐土上,这就导致他的宗教哲学出现许多荒谬的结论,也无法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但是,被许多人认为不值一顾的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为什么还是受到一些大哲学家的重视呢?不仅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与舍氏有密切的交往,而且凡是讲述现代存在主义历史的重要专著中几乎都要提到舍斯托夫和他的宗教哲学。其实,人们只要不是简单地看他的哲学结论,而是深入探讨这种哲学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这种看似荒诞而抽象的宗教哲学却包含着十分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确是非常尖锐而切中要害的。
自古以来,哲学的主流传统就是必然性崇拜,不管什么问题,只要能论证某种答案具有必然性,那就算到底了,就算站住脚了。对此人们也就自然地不再怀疑,不再反对,不再穷根究底了。在生活上也就顺应必然性而行动,并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自由。谁如果对必然性提出怀疑,就会被认为头脑有问题,甚至发疯了。其实,正如舍斯托夫所指出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学术上的底线,更不是生存中必须遵循的标准。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存中,人们如果像传统哲学所教导的那样,顺从所有的“必然性”,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学术上的停滞和生存上的逆来顺受。欧几里得几何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人们被它所限制,那还会有非欧几何吗?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们如果相信现实的必然性是牢不可破的“石墙”,那还会有什么社会进步吗?必然性是事物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所以人们只能顺从它,不然的话,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必然性是变动的,人对必然性的认识更是变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说认识必然就获得了自由,就要陷入荒谬。舍斯托夫反对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必然性,因为这种必然性带给人们的是人们无法把握的善恶不分的后果。可见,对必然性的解释如果离开了人的具体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而成为完全抽象的议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成为对现实的无原则的辩护。
舍斯托夫处于俄罗斯社会的空前大变动的时代,对于必然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着切肤的感受。沙皇反动政权在垂死挣扎,它在镇压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在宣扬自己的必然性,自己的强大和不可战胜。别尔嘉耶夫在狱中时基辅的宪兵司令就曾对他们说:“你们太不自量力,你们面前是一堵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 “地下人”也痛感“现实”的必然性是一堵使人窒息的“石墙”。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舍斯托夫反对不顾后果之善恶的必然性,而要求能够消除恶的真正的自由,这完全是从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正由于此,他也就坚决反对脱离人的生存状况的哲学说教,而要求哲学为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善而斗争。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干预生活的哲学,不应被视为荒诞之论。
舍斯托夫 - 著作
在约伯的天平上雅典与耶路撒冷
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
钥匙的统治
思辨与启示――舍斯托夫文集
舍斯托夫 - 评论
1.早在被放逐之前,舍斯托夫就与那帮代表普罗大众的知识人格格不入,在《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一文中,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勿抗恶”派,在舍斯托夫看来,都不过是一丘之貉,“皮萨列夫的终结处就是托尔斯泰的起点”。循着尼采所指明的道路,舍斯托夫把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雅典理性主义传统一锅端了,更遑论皮萨列夫或托尔斯泰这些俄国门徒。非但如此,舍斯托夫也没放过同时代的现代派文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后者在其巨著《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把“俄罗斯大地上最伟大的两大作家”当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极,理性与反理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二元对立的“理念”型作家,在《理念的统治》一文中,舍斯托夫的“魔眼”一下子就看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葫芦里贩卖的还是“康德哲学”,“康德不光不会支持寻找上帝的人,而且,他还以其‘公设’,把任何可能找到上帝的希望给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无疑是给了那帮希望从康德哲学中获得“上帝救赎”的俄国现代派文人一记耳光。现在可以晓得,舍斯托夫的流亡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开始了,既不同情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浪漫派,又蔑视彼得堡那帮贩卖“理性主义的轻薄救赎”的现代派文人,与现代文化人相龃龉就是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舍斯托夫当然就自我放逐出文化圈之外了。
2.舍斯托夫的“魔眼”太过尖,整个欧洲的希腊哲学传统都在他的冷嘲热讽之中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哲人有先见之明。《钥匙的统治》发表于1916年,两年之后,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出版了那本标题不详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与其说斯宾格勒针对的是西方,不如说斯宾格勒是在指证源自希腊的理性文明已走入境。钥匙的主人已经被希腊哲人们赶走了现代欧洲人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舍斯托夫也就成了流亡文化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舍斯托夫一生的努力就在于召唤“耶路撒冷”的重新归来,他一如先知约伯一般,“在恐惧与颤栗的深渊里,向上帝呼告”。
舍斯托夫逝世后,被称为“俄罗斯之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讲,惟一能懂并给他狠狠打击的哲人就是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修养自然不是彼得堡那帮又跳又闹的现代派文人比得上的。在自传中,他讲得明明白白,根本就瞧不起那帮整天在巴黎作悲苦状的现代派文人,宁愿忍受流亡所带来的孤独痛楚,也不愿堕入现代派文人的轻薄虚妄之中。真正的大哲学家,需要的是对手,舍斯托夫的逝世,对别尔嘉耶夫来说,不啻于少了另一双洞察现代精神的“魔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