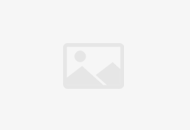普洛普的个人简介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Vladimir Propp,1895―1970)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艺术理论家,是苏联民间创作问题研究的杰出代表。 他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履历
1895年生于圣彼得堡,191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文史系斯拉夫语系俄罗斯语文专业。自1918年至1928年在列宁格勒的几所中学讲授俄语、德语和文学。他后来40年的学术生涯是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度过的,在那里他教授民间文学课程,并出任过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1966年他在该校退休。其间在国家地理学会、东西方语言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过学术工作。
学术成就
普罗普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国际学术界往往重视它在结构主义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巨大成绩,其实他在非结构主义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是相当丰富的。他的代表著作包括:《故事形态学》(1928)、《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1945 )、 《俄罗斯英雄叙事诗》(1955)等著作;此外他还发表了数量颇多的学术论文、评论文章,甚至还选编了数部民间作品集。
《故事形态学》该书是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家普罗普的开山之作。其写作初衷是为了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势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作者根据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100个俄罗斯故事进行形态比较分析,从中发现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规律,被20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学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人文学科众多分支学科的经典。
在这部著作中,普洛普不满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民间文学研究思路。他认为,传统的以叙事母题,如俄国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三兄弟”母题、“护身符”母题、“与毒龙搏斗的英雄”母题等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是一种不严谨的研究方法,因为一个母题下面可能包含若干子母题,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最小的不可再往下细分的单位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母题是一个可变项,它不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它出发点;真正科学严谨的研究应该从“不变项”或“常项”入手。为了达此目的,普洛普从人类学中引进了一个概念――“功能”,把它作为分析民间故事的最基本单位。功能单位是指人物的行为,行为之成为功能单位,依赖于其在整个故事发展中所具有的功用或意义。从这个原则出发,普洛普对俄国100个民间故事作了极为细致的研究,从中归纳出了故事的31种功能,并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1.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的不变的因素,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2.民间故事已知的功能数量是有限的;3.功能的次序总是一致的。
普洛普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功能概念:
1.沙皇以苍鹰赏赐主角,主角驾苍鹰飞向另一国度。2.老人以骏马赠送主角,主角骑马至另一国家。3.巫师赠给伊凡一艘帆船,伊凡乘船渡至另一国家。
普洛普认为,以上三个情节中人物身份虽有改变,但其基本作用或功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体故事中承担的职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可以被归为同一个功能单位。
在一篇故事中,除了功能单位,还包括其他因素,如功能单位之间的关联与重复,人物行为的动机在故事中是否明确表明等等。与功能单位结合最密切的因素是“人物”,人物与功能单位通常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性质相关的功能单位常常组成一系列连续的行动,这个连续的行动往往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物。特定的功能单位与特定的人物相结合,构成所谓的“行动领域”。
在不同的故事中,同一功能单位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同一角色也可以由具有不同属性的人物扮演,比如上面所举的例子:“沙皇以苍鹰赏赐主角,主角驾苍鹰飞向另一国度”,“老人以骏马赠送主角,主角骑马至另一国家”,“飞向另一国度”与“骑马至另一国家”实际上是同一种功能单位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沙皇”与“老人”是一对可以互换的人物,二者承担的也是同一个角色。同样一个角色,之所以在不同的故事中会由不同的人物来扮演,是因为地方习俗、宗教、仪式、文化背景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变形”之间的变换常常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普洛普称这些规则为“变换规则”。
功能是叙事作品的最小单位,功能之上的单位是“回合”。所谓“回合”,是由一系列功能单位组合而成的叙事单位。比如,故事的开始是灾难或反角的作恶,这算是一个功能,然后又经过一系列其他的人物动作也即功能之后,灾难消失,恶势力被消灭,最后是大团圆的“婚礼”――这样一整个过程,普洛普称之为“回合”。一个故事可能由一个回合构成,也可能由数个回合组成;回合之间也有不同的组织关系,可能是两个回合首尾衔接,也可能几个回合互相重叠,也可能一个回合未完之际又插入一个新的回合,总之没有一个定则。
通过对功能和回合的精细分析,普洛普总结出了一整套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则和叙事“公式”,他认为,用这些公式便可以代替所有的俄国民间故事,所有的民间故事都不过是这些公式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所有的算术习题都只不过是少数数学公式的不同演算形式一样。普洛普甚至还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依照这些叙事公式“创造”出新的民间故事。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民间故事形态学》这部被誉为结构主义奠基之作的名著,在其出版之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30年后它的英译本问世,这部著作以及它的作者普洛普才声誉雀起;叙事学大师如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布雷蒙、格雷马斯等,都从这部作品中汲取过营养。甚至可以说,这部书哺育了整整一代结构主义者。但是撇开它的重要性不谈,我们认为,作为一部文学研究论著,《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文学艺术是无限丰富、无限多样化的存在,任何一种概括或总结都无法穷尽它的全貌。《民间故事形态学》试图用几个有限的公式,将所有的民间叙事艺术一网打尽,这显然是一个很难实现的设想。并且,艺术的真正难解之处是其感染力和表现力,而不是其形式,即便我们将艺术形式分析得头头是道、十分完备,我们还是没有涉及最根本的问题所在:艺术作品的动人之处究竟来自何处?
普洛普的弊端也是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的弊端: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排斥社会、历史、作者的个人经历等对文艺作品的影响,把文艺研究封闭在一个形式的圈子里,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试图解答文学艺术的特殊问题的初衷。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初版于1946年问世,是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的第一部著作《故事形态学》的姊际篇,标志着作者对俄罗斯神奇故事由结构类型研究转入历史类型思路,在对神奇故事进行了结构形态描述,弄清它是“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后,就该转入下一步,去追寻它“从何而来”,即探讨它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们想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哪些现象(不是事件)与俄罗斯的故事相符合并且在历史现实中的根源”。本书旁征博引,大量引证了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地方性知识、方言故事以及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论述、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学问功底,堪称20世纪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典范之作。
普洛普的故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
普洛普的故事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在我国的流行而被认识与接受。但有将近20年的时间,译介、研究的内容大都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限于谈论他的《故事形态学》,而代表了其学术思想另一面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直在学者视野之外;进入新世纪,对故事学理论才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依然谈不上透彻的接受与研究。[1]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普洛普理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二手或三手的结构主义研究材料而实现的,而且主要集中在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一书的“人物功能论”及其对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上展开。其理论面貌一直被“结构主义”云雾笼罩,因而,我们称之为“雾里看花”的十年初步接受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普洛普研究开始触及细部问题,对已经凸显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当然,这个深入的过程也是与结构主义在我国的深入研究相伴的,主要涉及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我国叙事学理论的建构,普洛普学术身份认定和归属问题研究、学理运用等。但由于依据的材料依然是俄译的二手材料(也为数不多)或英译、法译的三手材料(占绝大多数),而且仍是只触及了普洛普理论的“功能论”方面,所以对普洛普的认识显得似乎得了“真经”,但尤未识其“真面”。因而我们称之为“亦真亦幻”的又十年艰难探索阶段。
进入新世纪(材料截止到2004年),学者开始以第一手俄文材料为依据,这大大推进了普洛普研究,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得以澄清,一些“盲区”得以展现,对其理论的运用也更加灵活自如,且经过加工、改造,普洛普理论在我国已经进入对多种叙事体裁作品的分析之中。[2]
评价
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者转向结构主义,他们的主要兴趣在许是传统和叙事结构啥时能共勉,他们的探讨动力主要与普罗普的方法相关。普罗普进行的先驱性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结构主义研究中仍旧结满果实。在欧洲民俗学,它的影响在最近的一批著作中仍旧明显。普罗普的分析方法也在儿童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中使用,同时它还应用于娱乐、电影、电视剧各个领域。普罗普的方法如此持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描述模式,他建立在低水平的抽象和事件叙事上的结构形态,提供了处理大文本式的完整叙事序列要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