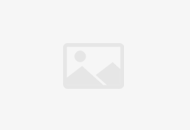石濂的个人简介
石濂(1662-1705),清画僧,为大汕和尚之号,字厂翁,号石濂,一作石莲,原俗姓徐,明遗民。明崇祯六年(1633)生,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籍贯江苏吴县(一说是江西九江)。著名作品有《侬梦寻欢竹枝词卷》、《离六堂集》等。
个人履历
石濂 清画僧。(1662-1705)。江苏吴县人,善画。人物生平
石濂为大汕和尚之号,字厂翁,号石濂,一作石莲,原俗姓徐,明遗民。明崇祯六年(1633)生,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籍贯江苏吴县(一说是江西九江)。清初曾与他交往甚密的大诗人王士祯(一作士G,字贻士,号渔洋山人)在其《分甘余话》中对此也莫辨真伪:“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看来,只有曾与大汕同行去过越南的挚友曾灿(字青藜,江西人,工诗词古文,“易堂九子”之一)所说最为可信,他为大汕的诗集《离六堂集》作序说:“和尚为吾乡(江西)九江人”。大汕早年情况仅知“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见潘来:《救狂砭语》)
历代画僧中,大汕可谓一位名噪一时的和尚。然而,有关评价他的一些资料,却是褒贬并存,褒之者认为他极可能是位反清复明志士(见庵:《大汕其人其像》);贬之者认为“他本是一个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见中华书局1987年版《海外纪事》前言,余思黎撰)。
大约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自称觉浪和尚(名道盛)法嗣。觉浪和尚是当时佛教曹洞宗在今南京一带的名僧。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曾从他学过佛。凭借这关系,加上大汕诗画兼擅的才能,很快便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岭南名士结交。又凭他善于制造古玩家具,工绘花鸟人物,得以投靠平南王府尚之信门下,以学问僧身份出入广州的官绅、士人中间。在尚藩势力支持下,不久就当上了广州城西长寿寺(今广州市长寿路附近,故址已毁)住持。于是大汕交游日益广阔,连省外名流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宋牧仲、万红友、田纶霞、王士祯等都与之交往,声势日盛。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安南(越南)阮福周政权遣使来广州,请大汕前往顺化主持佛事。于是,他不顾渡海之艰险远赴安南。在顺化,大汕被尊封为“国师”,授戒传法,曾一次就授戒1400多人。他所传扬的并不限于禅宗佛学,“大而纲常伦纪,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条分缕析,理明词畅……其为禅益政治实多”(阮福周《海外纪事序》)。实际上大汕所讲是佛道儒三教的杂糅,以适应阮氏政权的政治需要。不过客观上也起到“以中国之纪纲,变殊方之习俗”(毛端士《海外纪事序》)、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第二年秋,大汕携大量获赐赠的珍宝财物回到广州。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刊印出《海外纪事》六卷,内容是他在安南期间撰录的笔记、诗文,为后世留下了一部17世纪越南中部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及海上交通等珍贵而生动的史料。大汕此举,也是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要事。
大汕回广州后
用所得的财宝修建广州长寿寺、白云山麓弥勒寺、清远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按长寿寺本来创建于明万历年间,至康熙初已废。大汕善于园林布置,经他复兴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张渠《粤东闻见录》),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王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曾赞其“营造有巧思”,且亲书楹联“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潮”赠给大汕。又在其《分甘余话》笔记中,以“奇石”为题专门记载了长寿寺离六堂侧池上的一株奇石:“云产七星岩,其色黄如蒸粟,莹润如蜜蜡、琥珀……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此外,大汕还善营造家具器皿,“以紫檀、花梨、点铜、佳石”做家具器皿,“多巧思佳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著),时常赠送各方名流,备受赞赏。成就及荣誉
大汕“能诗善画”,他自重修长寿寺后,王渔洋、潘次耕(擅音韵、诗文及史学,撰有《遂初堂诗文集》及《别集》共三十九卷)、梁佩兰、陈恭尹等士大夫,常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大汕著有诗集《离六堂集》12卷,还喜欢作竹枝词。过去在香港举办的广东名家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他的《侬梦寻欢竹枝词卷》12首,其中如:
侬梦寻欢路万里,欢在江南亦梦侬;
欢梦来时侬梦去,欢侬依旧不相逢。
忍看花田欢燕,行人春日换春衣;
最怜昨夜花田月,如见夫君春燕归。
(季子:《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他善绘画,尤能画肖像,曾为诗人陈维嵩画肖像。可是王渔洋北归后突然憎恶起大汕,在其《分甘余话》的“妖僧大汕”中说他“常以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显然含有歪曲诋毁成分。现广州美术馆藏有大汕的《墨竹图》,写竹迎风挺立,“墨色浓厚,用笔潇洒利落”(见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很有才情韵致。他的画友有石溪和尚等。此外,大汕还是一位版画高手。据榆庵《大汕其人其像》一文,康熙年间大汕在自己的“怀古楼”刻印的《离六堂集》,卷首有大汕自己刻写的插图33幅,为反映其生平事迹的图象,是画笔极其工致、绝妙的版画,每幅都有当时诸名家的题诗。
秘密反清复明的志士
个人其它信息
大汕早年的事迹是个谜,而当了和尚却依然写儿女情长的竹枝词则属奇怪。更奇的是,大汕并非是个剃度落发的和尚,澳门普济禅院里祖师堂供奉着的大汕自画像,是个披发头陀相,#庵在其《大汕其人其像》中认为,这和在石涛年谱里《石涛种松图》中的头陀相仿,是很有寓意的,“这就是不肯剃发,不肯降清的意思”。
大汕交往虽广,然而深交的挚友却是像曾灿、石溪这样的明代遗民。曾灿早年曾参加过反清活动,与大汕特别投契(当然大汕本身也是明遗民),大汕赴安南是与曾灿一起去的。《离六堂集》的《序》也是由曾灿作的,“……大汕常与之谈当世之务,娓娓不倦,盖其天文、地理、兵法、象数,以及书画、诸子百家之技,无不贯通其源委。……今和尚之为人,岂与枯寂浮屠同日而语乎,抑有托而逃者耶?当其狂歌裂眦,淋漓下笔之时,怀抱渊源,空今旷古,此其志岂小哉!然和尚之善藏妙用者,又未知涯矣”,“余(曾灿)浪游三十年,欲阴求天下之奇士……而有奇士如和尚者,神龙莫测矣”。联系曾灿序文开首“往余与无可大师游,得参天界浪杖人(名道盛,字觉浪,大汕所从的法师),听其绪论,无一不归之忠孝,故其门下士,皆文章节义魁奇磊落之人,或至有托而逃焉者。”可见大汕是个蕴蓄不凡的人,托身和尚仅是表面遁迹空门而已。#庵先生分析序文,开首以“忠孝”、“节义”立论,文末归纳为“善藏妙用”,有暗示干“秘密工作”之意。
个人作品
《离六堂集》中有诗《自题寄友人》云:
满林黄叶一溪寒,白日青山卧懒残。
但恐云深人不见,聊将住处写君看。
曲折地反映了明亡后他的苍凉心境,和不甘清廷统治下的屈居现实,只好隐退空门。这与八大山人、石涛等遗民僧人大致相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
另外
看过《离六堂集》藏本的#庵先生认为,卷首的33幅自画的版画中,第三十一图为“制器”,看图意是制铁器,大汕既然知兵法,必定是制兵器了,不过在当时环境下不敢说明罢了,其意思是可想而知的。
《海外纪事》刊行不久,潘耒(1645―1708)(字次耕,吴江人)即针对该书和大汕,罗织了“种种不法之事”,主要是说该书“少实多虚”、“有伤国体”、“有碍法门”;大汕行事则“饮酒食肉”、“穷奢极侈”、“目若无人”、“大言欺世”、“存心险毒,以倾人陷人为能事”。(见潘耒《救狂砭语》)后来突然憎恶起大汕的王渔洋也在《分甘余话》中诋毁他,称之为“妖僧”,列其不法之处亦不过“常以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益#近之,于是无所忌惮”,“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珠之属,直且巨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无谁何之者”。看来也没有重大发现。而大汕被捕,却是按察使“许中丞(嗣兴)独恶之,辄逮治,诘其前后奸状,押发江南原籍,死于道路”。(见王渔洋《分甘余话》“妖僧大汕”)
关于大汕的罪状从来没有“谋反”一条,由此导引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一文的作者季子先生的推断:“关于大汕在海外活动,以谋推翻满清统治的证据,到现在已经没法找得到,就是在当时,也未必能找到,即使可以找到,地方官吏也只有设法消灭,不是回护大汕,只是回护当时与大汕往还的一班名流。当时大汕的交游,的确太广阔了。”连屈大均在后来也公开指摘他窃取别人诗句、欺世盗名。总之,都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可以理解,在当时“文字狱”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大汕的直接“罪状”谁敢点破?相反,指责和诬毁大汕却是一种恐受株连的自我保护措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