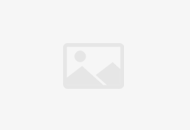尚春(艺术家)的个人简介
尚春,原名李春光,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969年10月生于秦皇岛,现工作生活于北戴河。
参展记录
2013年
4月,韩国国际艺术节联展,韩国,清州;
10月,“丹青天成”个展,798艺术区,北京;
2014年
6月,中国第十二届美展河北展区联展,石家庄;
6月,《中国国画家报》出版个人作品专刊;
2015年
1月,“尚春观念水墨”个展? M50文化创意园,上海;
7月,“纯化的自然――当代水墨邀请展”,北戴河;
7月,中国大连首届中国画联展,大连;
8月,“AGAINST NUCLEAR TESTING-FOR WORLD PEACE”联展,维也纳国际中心,奥地利;
8月,“我思?我在――尚春水墨个展”,享悦汇艺术空间,北京;
9月,“回归――山水美术馆开馆展”联展,山水美术馆,北京;
10月,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佛罗伦萨展览中心,意大利;
12月,作品参加北京保利十周年国际艺术秋季拍卖会,作品成交;
2016年
11月,“生命物证――尚春当代艺术展”,798悦美术馆,北京。
获奖经历
2015年
7月,中国大连首届中国画联展,大连,获优秀作品奖;
10月,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佛罗伦萨展览中心,意大利,获主席荣誉奖。
出版著作
《生命物证――尚春当代艺术》,内部资料,2016.11.1;?
《我思?我在――尚春新水墨》,内部资料,2015.12.1;?
《丹青天成》,内部资料,2013.11.1;?
《天开图画》,河北美术出版社,2013.1.1。
艺术评论
生命物证:尚春画集序言
文/贾方舟
“生命物证:尚春艺术作品展”主要由水墨和装置两部分组成。
尚春在水墨领域已经探索、实验多年。最初是学习各家,汲取各家之长。继而对水墨在宣纸上的千变万化、对笔迹墨韵的偶然性效果发生强烈兴趣。他也常画海边风景,因为他就出生在海边。从幼年起,他的生活经历就没有离开过大海、渔船和海洋里的生命。他有一句俏皮话:海就是我们家的冰箱,想吃什么海鲜可以随时去取。因此,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船”常常成为他想象的凭借,成为他演绎画面的视觉中心。但他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停留多久,他的天性聪颖,加以后天好学多思,动手能力强,从而使他在这个领域突飞猛进,很快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水墨语言套路,形成了以现代构成为基本格局的风格特征。
但尚春清醒地知道,仅以现代构成,还很难形成自己的个人面貌,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一种别人不曾使用的方式,才有可能改变画面的原有格局。
当尚春在树木的横切面看到一圈大于一圈的年轮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大自然生命意象的自我呈现吗?于是,他决定用拓印的方法来直接呈现自然的这一生命景观。在纸面上拓印出的不规则圆线条如水纹一圈圈扩散,呈现出树木在岁月流逝中不断记录自己、壮大自己的清晰痕迹;于是,树木的年轮就成为尚春新水墨的“原语言”。他的这个系列作品就是在这种“原语言”的基点上一步步衍化而来。
以年轮为主体的、一圈圈扩展开来的线组织和线结构,犹如音乐中的一个可扩展“主题”,而对这个“主题”的多个“变奏”――形的拼接、线的延伸、叠加、交错、开裂、缝合……则构成一个个对年轮的“变奏曲”,同时也构成对生命、对岁月的“咏叹调”。细想想,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年龄一岁岁增大,又一岁岁变老,再一个个离去,一个个新生,一代又一代,就这样,以循环往复的方式见证着生命的永恒。
尚春引入树木年轮所做的水墨作品,还只是对年轮这一充满岁月感的意象的借用。他的工作室的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拓印过和还没有拓印的木墩,他突然发现,其实,这些木墩本身呆在那里已经是一个作品,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在证明,自然本来就有记录自己岁月的方法和能力。尚春意识到,这些个“生命的物证”岂不正好用来“物证生命”的吗?不必拓、不必印,也不必画,这些个性鲜明的木墩,作为现成品就可以直接构成作品。于是,他的以木墩为媒介的装置作品由此而生。
由这一利用现成品的思路进一步扩展,使他在收集木墩的同时,又收集了很多形状像鱼的“松木明子”,当他将这几十只“松木明子”以《征》为题置于他原来收藏的渔船龙骨之上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又一番生命景象,尚春在无意间又创造出一种生命形式,仿佛一群鱼箭一般穿梭而过,以一种宏大结构和非凡气势展示出生命在进击中的辉煌。当然,我们也可以设定它们什么也不是,它们也不想是什么,它们就是“物”、就是“木”本身,就是从树的生命体中分离而来,就是一些形状天然的“松木明子”的集结,但它们却无疑是生命的物证!
在制作过程中,尚春对这些形状各异的“明子”展开创造性的想象,在它们身上随性置入一些异质金属小件,仿佛为满足这些“生命”对装饰的欲望,让人看起来多了一些优雅和亲近。因为人就是喜欢装饰自己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也就把这种欲望“移情”到其他生命体上。
我曾和许多艺术家交谈,发现他们对某些材料的特殊兴趣都和他们儿时的经历有关。以做榫卯结构出名的傅中望,从小看爷爷做木匠活,爷爷的心灵手巧、榫和卯无间的契合让他终身难忘;王怀庆作品中也常用到甚至是大面积用到不规则的木材片,而对这种极普通的材料的选择,却可以溯源到他小时候经常干的一件事:为生火炉劈劈柴!一斧子下去的那种快感终身挥之不去。工作后在剧团做布景道具又免不了大量的木工活儿。由此可知,尚春对“木”的敏感也非空穴来风,说出来就不必再多解释,他的父亲就是故乡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匠。他能把年轮引入他的水墨、把作为物质的木墩、明子转化为他的装置作品,也是在见证他自幼以来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
2016-8-12 ?北京京北槐园
游走于规律 ――尚春的水墨与装置
文/段君
年轮作为描绘对象,天生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它无疑象征着时间,暗示着岁月,但尚春并不是简单地表现时间,而是把对时间的体验同他的家族情感意识联接起来。在尚春的意识里,时间是有参照物的,如果创作者对时间的陈述所指示的参照物一无所知,那么对时间的表现也将毫无意义。在尚春的观念里,他自己的自传和家族的经历,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绝非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他在作品中试图融入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将艺术家个人、家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紧密相连,因此可以看出,尚春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他个人的情感因素,也包含了以历史为基础的种种社会观念。
回到艺术的本体层面,乍看上去,尚春的作品属于构成类的抽象水墨,但年轮实际上又是一个具象的图案,这其中存在某种有意思的悖论。贾方舟先生曾在纵观现代中国画的基础上,把抽象水墨的延展方向分为三种:一是从笔法中延展,如黄宾虹以笔法消解形象,凸显笔墨本身的韵致;二是从墨法中延展,如破墨、泼墨、泼彩、肌理;三是从构成中延展,强调画面分割,注重整体视觉强度,笔墨不再是视觉中心,点线面的构成关系才是画面主宰,代表人物可上溯至与石涛同时代的弘仁和尚,再到潘天寿、刘子建等人,均醉心于画面的分割组建。
尚春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第三种:即“从构成中延展”的抽象水墨,点线面的分割组建是尚春创立形式的主要手段与核心方法。尚春在近年的创作中,不仅着力探索画面各元素的构成关系,更是力图找到个人化的路径,他利用直线分割圆形的年轮,或是安排块面截断年轮,或是借助年轮本身的交织与离散,在画面上表现视觉形式的各种变化。能够发现,尚春在多年的文艺生涯中,积累了形式美学方面的必备素养,尤其是2005年尚春还曾实践过摄影,摄影的形式、构图、光线等等,对水墨的平面形式、画面的构成组织等方面无不起到“润物细无声”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尚春以大量的精力,打入了语言规律的领地,但很显然,尚春的追求并不是语言规律的熟稔,而是更加自主的表达,当语言规律对他的表达产生束缚的时刻,他完全可以置之不顾,将语言规律放在一旁。
为了更完整的表达,尚春除了在水墨的平面领域不断摸索,还将水墨与装置两种媒介结合起来进行尝试。中国现代水墨依然具备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水墨装置,完全能够充分承载今日观念的表达。当年李小山断定中国画穷途末日,栗宪庭认定抽象水墨将是中国画发展的又一峰。时至当前,水墨装置,或者说是“往空间中延展”的水墨,显然将更适合水墨艺术家展现更多的智慧和创造性。尚春并非水墨专业出身,这使得他可以不以水墨媒材为中心,甚至可以在不需要它的时候果断地放弃它,毕竟尚春对水墨作为媒介并不负有使命感,表达的精确和彻底,才是尚春所需要的。
说起尚春对装置这类空间形态的感觉,其实可以追溯至1992年他自学根雕,迄今二十余载,虽然根雕的惯性思维无法完全剔除,但从乐观的方面讲,也促成了他对材料和空间的把握。装置的创作虽然也有规律可循,但与绘画相比较,毕竟限制相对松散,可发挥的空间巨大,尚春凭借个人的感性和直觉,在创作时无所顾忌,尽管最终的作品偶尔不符合装置的通常语法,但反而时不时令人感觉耳目一新。不过,尚春也有循规蹈矩的时候,他最近创作的一件装置作品《征》,颇为遵守装置创作的规律,《征》体量巨大,长度达到十三米,高近四米,是在一条废弃的船体骨架上插上数十条铁管,铁管上又锁扣住60条如同鱼型的松木明子,整体上看去,仿佛一群大鱼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在船体骨架的支撑下,为了一种信仰而勇往直前。尚春特意用到的船体骨架,通常称为龙骨,是中国造船史上重大的发明,比欧洲最早在船舶上使用龙骨结构要提前数百年。尚春选择和使用它,显然是考虑到龙骨承载了本土历史和本土精神,能够更恰当地表达他对本土文化的诠释,同时也借助船体骨架的巨大体量,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特点。总而言之,尚春多年来游走于规律,在水墨、装置等领域,创作出了许多既在规范之内,同时又经常出离于法则的作品,为当代艺术增添了更丰富的多样性。
2016年7月
生命线:尚春的水墨与装置艺术
文/葛秀支
尚春的水墨与装置作品,在我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线”:盘绕在年轮中的“线”以及线的延伸与交织。树木的年轮是树木给自己做的生命记号,它很像通常我们在手相中说的“生命线”。生命线的长短预示着人的寿命的长短,如同年轮的多少标志着树木寿命的长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尚春的线,就不只是一种单纯形式意义上的线,而是赋予了生命意蕴的“生命线”。
尚春通过“拓墨”的方法将年轮的线转移到画面上,再辅以“弹线”和画线的方式,产生出独特的画面效果,将水墨的边界拓展到一个新的维度。
尚春的“拓墨”,首先是基于材料的选择。对于自小便熟悉木匠活的他来说,当木墩上的年轮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那一圈圈美丽而神秘的线纹已经是不二之选了。木墩上环环绕绕的年轮,是时光的雕刻,是岁月的留痕。他在拓印之前,首先要对木墩上的“年轮”做特殊处理。经过处理后的年轮,形成凸凹不平的肌理。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拓印,将年轮的自然肌理转移到宣纸上。
与此同时,他还借用木匠“弹线”的方式,即从墨斗中拉出一条墨线,用手轻轻一弹,在木板上留下一条直线。在宣纸上“弹线”与画一条线完全不同,“弹线”显得那样简单、机械,极富刚性。同时,“弹线”的两侧会出现许多类似射线一样的短线和大小不同的墨点。“弹线”需要一定的力度,可轻可重,这个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在纸面上形成的效果非常具有识别性。年轮的天然肌理与“弹线”相交相叠,形成别样的效果。可见,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确立,要靠新材料和新技法的支撑。当代水墨边界的不断拓展便是材料语言的不断推新,但同时又保留了水墨特有的趣味。
“弹线”作为一种作画方法,已经注定了尚春游离传统的笔法。但是“弹线”并非是尚春的发明,他只是对木匠画线这一特殊方法的挪用。他的父亲是家乡远近闻名的木匠,并熟练木板雕刻。他自小耳濡目染,对于木工的工序和技术都比较熟悉,自己也曾亲自动手参与制作。“弹线”是木工中一道必经的工序,没有这条直线,下锯无法做到精确。尚春将传统木工活儿的技法转换到绘画中,引出的便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语言的变革。在他的作品中,年轮的拓印与弹线结合,使弧线与直线形成对比。线与线之间的撕裂、缝合与纠缠,使画面形式更加具有视觉冲力。
在拓展水墨语言的材料中,也曾有艺术家使用“弹线”,但尚春与他们有所不同。尚春水墨中反复出现的拓印年轮与弹线,是符号化了生命线的延长与隐喻,是将传统水墨引入到了当代语境的一种新的形式试验。他在向世人展现当代人的别样情怀之外,也保留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对传统水墨的线的挚爱与不舍。
在尚春的装置作品中,仍旧以这样的“生命线”为叙事手法,使用木墩做装置作品。尚春还利用松木明子做了一组类似“飞鱼”的装置作品《征》。尚春以渔船的“龙骨”为基座,将一条条“飞鱼”置于其中。
这些“飞鱼”穿行于浩瀚历史时空,讲述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从而又形成一条无形之线,连贯了遥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组装置艺术作品,使得尚春的水墨语言表现形式实现了在空间层面的有效延伸。他对于材料的选择,令我暗自称奇。因为,松木明子是红松树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化后留下的精华,不腐烂、不怕潮湿、不怕浸泡,散发着松脂香气而且材质坚硬,色泽黄红。它们与年轮一样,具有天然的纹理,极具沧桑之感、铿锵之美。
尚春对其父亲、祖父充满了崇敬与感激。他在《祖父、父亲和我》作品中,以凸显“生命线”的方式,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情,用“生命线”穿越时空,将祖孙三代连接在了一起。
尚春通过材料的转换与挪用,强化了其作品的视觉张力,植入了个人观念,拓展了作品的生命意蕴。相信在这个方向上,尚春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2016年8月于北京
存在之语 ――尚春的“年轮”艺术
文/徐虹
来自遥远山地的巨木,被海边等待的艺术家截成一段又一段。于是他就像探究海洋一样,探究这山林的象征物体。大树新鲜的剖面犹如被开启的密盒,那层层密密的环形年轮,雕刻着大树的生命历程。就像医生剖开人的身体,艺术家为山林中的生命之精巧神秘,为它在天光下闪现的自然辉光而赞叹。它是生命密码,藏匿着大自然万千消息,人类的科技手段实际上难以完全破译。与自然交流就像面对大河取一瓢饮,就能感到生命充满新鲜感,就有了再生的希望。因为我们是在与大自然对话中逐渐变成现在的“我们”。
尚春作为艺术家,是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倾听自然的窃窃私语并和自然对语。他对事物异常敏感,能够发现事物形式细微的变化和形态的差异。他的作品朴素而单纯,厚重而富有生命意识。比如他将树的年轮和生命的代际替换联系的意图,比如他父亲的木工手艺与从小随父亲打下手的经验和生存体验,不仅给他思想和艺术观念带来关于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思考比照,而且是他的艺术形式的源头。之中有画家的意愿,也有生存的记忆,更有希望和期待。这些,无疑会在作品实现过程中得以加强和集中。所以看似单纯的作品自有形式带来的无穷意味,让观者根据各自的生存经验和学识修养,去解读,去对话。换句话说,艺术不就是在人生的舞台上通过一句台词或一段乐音,留下瞬间的痕迹吗?绘画和雕刻,不就是通过线,形体,一片色彩,表明世界在内心的位置吗?存在之语是那样遍布于普通事物之中,无论是在第一自然,在森林在大海,在天空在宇宙;还是在第二自然,在你我他的日常琐碎中,都有深厚而恒久的的持存。这大概就是尚春那些看似单纯直白,而又意味深远的作品留给我的遐思。
感受、处理、转换……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必经之路。这种创造是一种艰苦辛劳的付出,经常要将已有的事物重新组合与重新分离。在分分合合,覆盖再显现中,形式的真实才得以呈现。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像脱胎换骨的生命一样,它带着密码,生长出新的样态。所以,他对树木年轮的处理过程,实际就是艺术观念和语言形式的探索过程。他以大量时间和精力,琢磨如何将树木的年轮转换为艺术形式语言。比如在表现手段上是平面、立体,是拓印、描绘,还是摄影或装置……他要准备大量的材料作表现的铺垫,于是他像手持钻具的开矿者,在地层深处勘探挖掘宝藏,或双手荷锄的农夫,在大地表层垦殖播种作物。他在树桩剖面上实施砍、削、劈、琢、烧、磨等诸多手段,让“年轮”浮出剖面,才有雕刻般的可触摸之感,才能成为拓印的“基底”,成为物体所呈现的“现场”。一般观众并不能根据画面完成的效果想象这些曲曲折折的过程,但这些过程在作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张意味隽永的画面,就是有无数看不见的“过程”的痕迹所组成,在这意义上说,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
画家每次将这“雕琢”的树木年轮轨迹拓印在棉质的纸上,也就如一个清晰的声音穿透迷蒙的时空而来到意识之中;像从混沌之中受到一次召唤,存在之相从隐蔽之处显现出来。这个显现是艺术家进一步的“看见”,也就是根据自然留下的疏密肌理和结构层次再一次的“发现”。他凝神聚思,展开想象,从心灵的深处到经验的表层,从已有的审美积累,到日常的点滴印记,都在寻找和贴近符合这一召唤的形式,那就是再次的创造,为的是破译这年轮对他的感情含义。这含义要从已有的向心圆,已有的周而复始的轨迹,解读和寻找与生命之圆切合的缘份。
所以,一件作品之所以能有独立的形式语言,贯穿其中起作用的是艺术家的“思”。而这“思”在画家选择树木年轮作为作品基础时,已经关联到了形式的构成。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圆形和半圆,残缺的圆,多形态的圆,呈现的是一种哲理象征。这种象征也可以联想到漫长的人类文化传统,那种对于圆与生命的美好联系,显然古人和现代人一样,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发现了生命具有的独特形式,并赋予这种形式某种文化意义。但艺术家的使命是对生命样式的感性提炼,一种与自身活力相关联的形式要素,因而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比如圆形是人类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中概括出来的形式,一种完美、自然,天衣无缝,极富包容性的象征符号。但艺术家需要对从树的年轮中获取圆的形式重新运用,以彰显自己的情感结构和艺术趣味。比如,拓印下来的圆形多重叠置,错落有致疏密相间,形成前后空间关系和层次结构,用以表达时间和空间中的生成转换意象。
有些圆形被截取后,艺术家加入一些墨线,有勾勒也有晕染,有坚实如磐石划痕,也有如飞鸟空灵超逸。有交叉的线,有直线和弧线;有湿重的线和爽劲的线。有一种特别的“线”与主题关系更为密集,那是木工用来规范作业的“弹线”。这种线用棉料制成能吸墨,两头拉紧,中间用手指一弹,连接两点的墨线就落在物体上。这既连接事物,也分开事物。艺术家用此方法连接不同的圆或者分割同一圆为不同空间。这种线条的特殊是作为事物经纬法则的存在,它的意义在于以第二自然的方式并存于第一自然之中,成为存在的不可分内容。所以,就像人们在建筑和木质结构上感到的那样,这种线有份量,有温度和生命意象,它既来对自然的提炼,又发展于进化的平衡形式。这种手段的运用,使得创作者对自然与人的关系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联系,从日常生存经验中获得存在之语。
徐虹,2016年7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