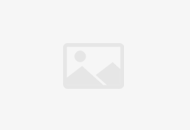祁济时的个人简介
祁济时爵士,KCMG(英语:SirMichaelDavidIrvingGass,1916年4月24日-1983年2月27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65年9月至1969年1月出任香港辅政司兼行政及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1969年3月至1973年10月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祁济时在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早年于西非黄金海岸政府供职,官至内政部常务次官。在1958年至1965年间,他调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布政司,此后出任香港辅政司。在辅政司任内,他与何礼文及姬达等港府官员应对六七暴动,并在1967年6月至9月期间暂代戴麟趾爵士署任港督一职,设法主持大局。在暴动期间,他对滋事的左派份子采取强硬态度,从而有效控制局势,但也因此成为左派阵营口诛笔伐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祁济时在1969年卸任前夕获英廷授予KCMG勋衔,以肯定他在任辅政司期间的表现。祁济时在1973年结束殖民地生涯,返回英国定居,晚年曾于1977年至1981年间出任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并热心参与研究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生平
早年生涯祁济时在1916年4月24日生于英国多实郡韦勒姆(Wareham),父母分别名叫乔治?艾文?加斯(George Irving Gass,1883年-1947年)和诺拉?伊丽莎白?孟斯塔德(Norah Elizabeth Mustard,1887年-1945年)。祁济时是家中五名兄弟姊妹中的长子,其余四名弟妹分别是布莉吉特?艾文?加斯(Bridget Irving Gass,1917年-2009年)、梅里?艾文?加斯(Murray Irving Gass,1922年-1942年)、伊恩?艾文?加斯(Ian Irving Gass,1922年-1991年)和E?N?I?加斯(E. N. I. Gass,1928年-)。
虽然生于多实郡,但祁济时自幼已随家人迁回 萨默塞特郡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附近原本居住的小镇百利沃顿(Butleigh Wotton)。他早年入读当地位于 布鲁顿(Bruton)的英皇学校,毕业后考入 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1937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再入读 剑桥大学 皇后学院,并于1938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祁济时后来又获得基督教堂学院颁授 文学硕士学位。
殖民地生涯西非及西太平洋
大学毕业后,祁济时旋于1939年加入 殖民地部从事政务工作,同年7月获派往 西非殖民地 黄金海岸出任助理 民政专员,是战前最后一批派到当地的 官学生。可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年9月爆发后,他随即应募入伍,服役于皇家西非前线部队(RWAFF)辖下的黄金海岸军团第三营。在二战期间,他曾获派到 东非 肯尼亚等地和 缅甸各处作战,因表现英勇而获两度传令褒奖,一直到1945年二战完结后,他才以 陆军少校身份从军中退役。
在1945年,祁济时返回黄金海岸的殖民地政府出任民政专员,并一度在1946年被借调到劳工处徙置科,参与战后的重建工作。在1951年,他获擢升为二级政务官兼辅政司署高级助理秘书,并在1953年进一步晋升为一级政务官,同时出任 阿散蒂地区的助理区域理民官。祁济时在1956年被调回殖民地首府 阿克拉,出任内政部常务次官。黄金海岸在1957年宣布独立为 英联邦王国,并更名为 加纳后,他留任常务次官一职至1958年,而加纳则在1960年更迭国体,成为 共和国。
祁济时在1958年调往西太平洋地区,担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 布政司,并在英属所罗门群岛的首府 霍尼亚拉办公。在任内,他曾于1959年、1961年、1963年和1964年多次署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一职,曾与他共事的还包括在1961年至1964年间出任高级专员的戴麟趾爵士。在1960年的 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英廷向他颁授CMG勋衔,以表扬他多年来在海外担任公职所作的贡献。
局势日益动荡
在1965年3月,英政府宣布委任祁济时接替退休的 戴斯德出任香港辅政司兼 行政 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与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公署供职的时候一样,他的 港督上司正好也是刚于1964年4月才上任的戴麟趾爵士。祁济时同年5月在 香港作短暂逗留后,于9月正式上任。与戴斯德不同,祁济时长年在 西非供职,未曾出仕香港,只曾在1960年访港旅游,因此被市政局民选议员 叶锡恩等人质疑他对香港缺乏认识,政府内部对其空降也有微言。虽然如此,他很快就融入香港的社交圈子,并掌握和了解香港各方面的事务。
应对连串 暴动是祁济时在辅政司任内最大的考验。在1966年, 中国大陆爆发 文化大革命,使位处中国边陲的香港也变得日益动荡不稳。就在他上任后不久, 九龙地区在1966年4月因为 天星小轮头等收费上调五仙至港币两毫半而发生暴动,期间港府一度宣布实施 宵禁。暴动过后,港府虽然发表报告承认香港警队的 贪污问题是暴动成因之一,但叶锡恩仍批评祁济时不了解问题严重性,也“不愿意倾听可以了解真相的事情”。不过,祁济时事后公开反驳叶锡恩的言论,他强调警队贪污问题只局限于初级警务人员,认为问题并不如想像般严重。
应对六七暴动
继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后,香港在1967年5月再因为东九龙 新蒲岗一家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而引发工潮,工潮在 左派的介入和“革命”风潮席卷香港的情况下,更演变成为持续大半年的 六七暴动。从5月6日起,发动工潮的工人开始与警方发生零声冲突,局势更随着加入人数不断上升而恶化,迫使港府在5月11日宣布东九龙实施宵禁。在5月16日,左派团体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号召挑战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构成威胁。
面对左派暴动,祁济时采取强硬姿态应对,在5月17日的立法局会议上,他强调“港府决心维持秩序”,并表示已责成劳工处长化解引起暴动的劳资纠纷。可是,骚乱此后仍然持续,在5月下旬进一步蔓延至 香港岛的 中环等地,港督府外更沦为左派张贴 大字报的地方。为免局势失控,港府随后派出 防暴警察拘捕滋事者,以及一度对香港岛实施宵禁。港府复于5月24日颁布紧急法例,禁止公众进行煽动性的广播和集会,随后又于6月1日起禁止公众张贴煽动性的标语。在5月31日,祁济时再次于立法局内发言谴责暴动,他形容连串暴动是“少数人使用卑鄙的恐吓和暴力威胁所造成”,同时重申港府“决心竭尽全力制止这种恐吓和暴力”,表明不会退让。
可是踏入6月份,左派团体不单发起示威和暴动,还策划各行各业的罢工和罢课,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在这个时候,港督戴麟趾爵士却在6月25日因病与家人返回英国休假,祁济时遂出任护督一职,设法主持大局。除他以外,华民政务司 何礼文也获任命为署理辅政司,而防卫司兼港督特别助理 姬达则获任命为增设的副辅政司(特别职务),祁济时、何礼文和姬达三人遂成为港府应对左派暴动的核心决策人物。当时英政府及港府内部一度讨论英国应否放弃香港,但几经何礼文等人在行政局内陈情,才促使英政府决定继续留守。
祁济时接手主持大局后负责领导行政立法两局,处理过不少危机。在7月8日,中港边境发生沙头角枪战, 中国民兵突袭驻守边防的 香港警察,造成五名警务人员殉职。事件发生以后,祁济时除了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慰问外,又宣布对 沙头角短暂实施宵禁,和改由驻港英军派驻踞喀兵驻守沙头角边境一带,在8月11日,港府还决定关闭中港边境。虽然沙头角枪战使中港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但祁济时在致英联邦部(Commonwealth Office)的内部函件中认为,事件主要由一些受中共地方政府支持的民兵发动,只属于个别事件,相信与 北京方面的 中共领导层无关。
另一项使港府大为头痛的危机,是左派份子由1967年7月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他们除了针对政府官署发动袭击外,寻常街道以至公共交通工具都成为袭击对象。左派份子放置土制炸弹的行动一直到同年10月才告中止,期间他们在全港一共放置了8,074枚真假炸弹,当中1,167枚属真正炸弹。这些土制炸弹除了使警务人员疲于奔命外,部份人更因此殉职,而不少普通市民也无辜成为受袭对象,使到左派暴动进一步失去民心。面对土制炸弹的威胁,祁济时没有妥协,并且出动警队高调搜查左派份子各处据点,以及大举搜捕左派滋事份子,当中包括在8月4日向访港英军 航空母舰借用 直升机,攻入左派份子在 北角 侨冠大厦的阵地。在紧急法例生效下,部份参与策划暴动的人士更被递解出境。
祁济时认为,港府虽然大举搜捕左派滋事份子,但从北京方面“出奇地温和”(suprisingly mild)的反应推测,他结论中方无意派 解放军挥军香港,意味港府可以放心镇压左派暴动。此外,在与英联邦部的内部书信往来中,祁济时批评香港的左派 报章在暴动期间煽动舆论情绪、报道虚假新闻和多次恶意中伤港府,但考虑到《 大公报》、《 文汇报》和《 新晚报》等主流左派报章由中方控制,因此他向英政府建议港府先向一些独立的左派报章采取行动,以收阻吓作用。不过,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格雷事件”中,香港法院在7月19日以煽动暴乱罪名判处 新华社记者薜平入狱两年的行动,却直接导致中方在7月21日拘禁 路透社驻北京的英籍记者 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反映中方也有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虽然如此,尽管英政府内部同样担心对付左派报章可能会触怒中方,但祁济时的建议仍旧在8月4日获得英联邦部的正式批准。
在得到英政府支持下,祁济时在8月9日出动警方搜查多间左派报馆,并拘捕《香港夜报》社长胡棣周、《田丰日报》社长潘怀伟、《田丰日报》督印人陈艳娟、南昌印务公司董事长李少雄和南昌印务公司经理 翟暖晖合共五人,而《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独立左派报章均被勒令停刊。祁济时查封左派报馆的行动成为后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主要导火线之一,事件中,为了报复“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大批 红卫兵在8月22日包围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至晚上时份更以武力冲入代办处,纵火焚烧大楼和停泊的汽车。
由于祁济时在六七暴动期间指挥港府强硬对付左派份子,因此他一时成为左派阵营口诛笔伐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以“斗委会”为首的左派阵营曾经在坊间派发单张,列举祁济时的“十大罪状”,当中包括“把香港变成侵越反华基地”、“遏制 毛泽东思想传播”和“迫害爱国新闻工作者”等等;此外又在全港闹市张贴街招,表示要向祁济时发出“通缉令”,要求他认错道歉,并警告他“当心问绞”,而部份激进的滋事份子更在市区放置 棺材造型的土制炸弹,扬言要把棺材送给祁济时使用。
这些针对港府和祁济时的行动虽然广为香港的左派报章报道和宣传,但随着港府强硬对付和搜捕左派滋事份子,再加上左派的激进行动和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为主流报章和舆论所猛烈抨击,暴动并不获普遍香港市民支持,而香港局势在9月以后也终于逐渐得到港府有效的控制。在9月24日,港督戴麟趾返港回任,在动荡时期领导港府前后三个月的祁济时遂在9月27日离港休假,一直到1968年1月26日才结束休假返港。在展开休假前,祁济时还在立法局通过了《烟花爆竹紧急条例》,从坊间回收大量 烟花 爆竹,并禁止市民私自管有和燃放烟花爆竹,以防这类物品落入左派阵营用以制作土制炸弹。
就在祁济时展开休假后不久,鉴于香港的左派暴动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 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愈演愈烈,为免出现反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阵营下达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扰攘香港近七个月的六七暴动才告全面平息。
暴动平息以后
汲取六七暴动的经历,祁济时在1968年提出兴建大榄女子监狱和专门收押男性犯人的壁屋监狱及惩教所,以强化监狱系统,两所监狱后来分别于1969年和1975年落成启用。此外,考虑到 青少年向心力不足是部份青少年参与暴动的原因,祁济时与 警务处处长伊达善等人在1968年研究设立类似英国三军招募少年入伍受训的计划,为合适的青少年提供公民及纪律训练,同时为他们安排社交和康乐活动,从而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在祁济时等人的构想下,港府复于1973年正式成立 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专门为15至17岁的少年提供升读传统 中学以外,另一个以专业训练为核心的升学途径。警察少年训练学校一办17年,至1990年才告停办。
祁济时也有份审视 香港地铁的兴建计划。早于1966年2月,港府已委托 英国的费尔文霍士顾问工程公司(Freeman, Fox, Wilbur Smith & Associates)就发展集体运输系统进行研究,顾问公司复于1967年9月发表《香港集体运输研究报告书》,草拟了地下铁路的兴建蓝图,有关报告书其后由祁济时于1968年2月送交立法局审议。虽然港府当时的工务司 邬励德曾表示希望可以在1968年底为香港地铁的兴建作最后决定,惟建造方案一再修订,使工程多次延迟。一直到祁济时卸任后多年,港府才在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下,于1972年成立地下铁路临时管理局,而首条地下铁路要到1975年11月才正式动工兴建。
祁济时的其他工作还包括在1968年5月出任1970年世界博览会香港馆总监,负责为暴动过后的香港向外资推广经贸商机。这次博览会是香港自六七暴动以来首次参与的 世界博览会,但是到博览会于1970年在 日本 大阪正式开幕的时候,祁济时已经卸任。
在1968年10月,港府宣布祁济时即将卸任辅政司,同时宣布他会出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祁济时在1969年1月26日正式卸任,结束前三年多的辅政司生涯。在卸任当日,他从 皇后码头乘座“ 慕莲夫人号”横渡 维多利亚港,随后在 九龙的 启德机场登岸,再乘搭 英国航空班机返回英国,并在登机前获各界人士在场送别。他在临行前又接受记者访问,表示“对香港前途深具信心”,相信香港的“工商业将会继续繁荣”。
除了在六七暴动期间,祁济时也曾经在1966年6月29日至8月28日、1968年4月24日至5月17日、以及同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出任 护督,代理港督的职务。在出任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前夕,为表扬和肯定祁济时在香港辅政司任内的贡献,英廷在1969年元旦授勋名单中宣布向他颁授KCMG勋衔,成为 爵士。至于祁济时遗下的空缺,则由 塞舌尔群岛 总督 罗乐民爵士接替。
西太平洋高级专员
在英国作短暂逗留后,祁济时在1969年3月重返英属所罗门群岛首府 霍尼亚拉,正式就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在任内,他负责在动荡的局势下推动政制改革,并参考伦敦郡议会的运作模式,于1970年为所罗门群岛引入新的宪法。在新宪法下,当地设立一个全新的管治议会(Governing Council)以取代原有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而透过新的委员会制度,所有管治议会议员都可以兼任议会辖下的五个委员会委员,从而参与政策的制定。然而,由于舆论认为新的宪制并不符合当地需要,结果他在1973年卸任后的翌年,当地再引入新的宪法,以更为普及的威斯敏斯特式部长制取代原有的委员会制。
此外,祁济时也积极推动英属西太平洋领地的解体,在1971年,吉尔伯特及埃里斯群岛(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不再受高级专员管辖,改为直属于英国外交部,为吉尔伯特及埃里斯群岛连同领地内的广东及安德贝利群岛(Canton and Enderbury Islands)和 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等地,在日后独立为 基里巴斯、 图瓦卢和 瓦努阿图铺路。
值得一提的是,祁济时不单在任内拜访各大群岛,更是最后一位坚持造访官邸的宾客必须身穿 晚礼服的高级专员。有趣的是,由于当地并不流行穿晚礼服,因此他曾经打趣地表示,每次在官邸出席不同的场合时,总会发现男宾客身穿的晚礼服外套都十分眼熟,估计当地仅有的几件外套都在访客之间流转借用。
晚年生涯虽然身在西太平洋,但祁济时任内仍不时被香港舆论提及,特别是被舆论盛传与 罗乐民爵士一样是 港督戴麟趾爵士的热门继任人选。有关传闻在祁济时于1970年12月休假访港的时候更为尘嚣甚上,及至1971年,英政府公布 外交官出身的麦理浩爵士将接任港督后,有关传闻才得以平息。祁济时在1973年9月卸任高级专员一职,展开退休生活,并由香港民政司 陆鼎堂接任。在卸任返英途中,他选择再一次路经香港,与各界友好聚旧。
祁济时返英后定居于 萨默塞特郡桥水镇(Bridgewater),后于1977年至1981年间当选为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晚年的祁济时热心参与研究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在郡议员任内曾于1978年至1981年间身兼郡议会的图书馆、博物馆及纪录委员会主席,另外也曾参与萨默塞特郡考古及自然历史学会的工作。祁济时在1983年2月27日于萨默塞特郡猝死,终年66岁。
个人生活
在殖民地供职多年的祁济时一直未婚,至退休后的1975年,才以59岁之龄在萨默塞特郡迎娶比他年轻24岁的伊利沙伯?艾克兰-胡德(Elizabeth Acland-Hood,1940年3月2日-)为妻,夫妇俩膝下并无子女。祁济时爵士夫人系出名门,是萨默塞特郡的世家氏族,其任职大律师的父亲约翰?艾克兰-胡德阁下(Hon. John Acland-Hood,1906年2月11日-1964年11月2日),是前任 财政部政务次官圣奥德理斯勋爵(Lord St Audries,1853年9月26日-1917年6月4日)的幼子。
祁济时爵士夫人的娘家在萨默塞特郡具深厚的政治势力,其艾克兰-胡德家族在 19世纪一直控制着当地西萨默塞特选区的 下议院议席。祁济时除了曾任郡议员外,他的妻子也曾在1985年至1997年间出任萨默塞特郡议会议员,及后更于1994年出任郡督、1995年出任副郡尉、1996年受封 太平绅士、以及由1998年至今出任萨默塞特郡郡尉。
在个人兴趣方面,祁济时爱好园艺、 兰花和 摄影,并把不少以丛林和兰花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制成 圣诞卡寄赠亲友。祁济时对 鸟类学和关注萨默塞特郡的地方历史也有相当的兴趣,他生前也是 伦敦东印度会和香港会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