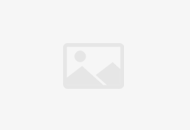沙岚的个人简介
沙岚,男,1949年2月生于上海市,江苏南通市人,汉族。安顺书法家协会会员。其工作业绩和传略入编《世界名人录》。
基本内容
沙岚:男,1949年2月生于上海市,江苏南通市人,汉族。1969年3月赴贵州省安顺地区紫云县插队落户。1971年抽调上来,先后在紫云县、安顺市任教,曾任安顺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高级政工师、贵州省教育学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安顺书法家协会会员。其工作业绩和传略入编《世界名人录》。从小酷爱书法艺术,楷从颜、欧体入手,行草以二王、唐寅、文征明为范本,崇尚潇洒俊逸风格。从教三十五年,闲暇之余,笔耕不辍,著文寄情,习字养性,赏石寓趣。
峥嵘岁月稠――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一、插队落户: 特定年代的历史现象
“老三届”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和一个专用名词。我是那个特定年代无数个66、67、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它意味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那个年代,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每个家庭细胞,必然至少有一个“老三届”生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远离城市,分赴全国各地穷山僻壤,去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艰苦历练。
我于1968年7月高中毕业于上海市光明中学,随即而来的就是长达半年多令人烦躁不安的“待分配”。按当时学校“工宣队”宣布的政策,只要原籍有亲友且生产队同意接收的,可以“回乡”插队。于是,在这半年中,我三次往返于老家江苏南通,通过二姐(她幼时过继给姑妈为女)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说通村干部和某些亲友,才勉强同意接纳。殊不知,政策又骤起变化,说是老家光有母系亲戚不行,非要有祖父母、叔伯辈的亲戚同意接纳才可以投亲落户。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候的我性格内向,身体羸弱,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糊涂人,亲生母亲1960年早早病逝,大姐从安徽安庆退职回来在街道里弄生产组工作,继母又是一个厉害角色,她带了三个孩子到我家,家境的贫苦拮据和血脉关系的隔阂紧张可想而知。加上父亲的身份是“小业主”,年轻时曾稀里糊涂被人介绍参加过一个所谓特务外围组织(其实只是填了一个表,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于是乎,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一个反复交代、被批斗,而最终又以“人民内部矛盾”结论处理的“老运动员”。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家庭中,从祖父、母亲去世后,我稍谙世事起,就几乎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亲情和呵护。
也正因为有如此困苦而复杂的家境,老家南通亲戚那边,既担心我从小缺乏锻炼,手无缚鸡之力,不胜农活,又唯恐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累赘。一张张白眼势利的脸嘴,使我较早地尝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的苦痛。我放弃了回乡南通插队的努力,毅然决然报名到贵州“插队落户”。“申请书”刚刚送上,“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安置的地点是:贵州省安顺地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山区紫松公社一大队那王生产队。倾刻之间,我的名字从此在无比金贵的上海市户籍中注销;这一注销,使我在贵州安顺生活、工作了整整四十年。
我异常清楚地记住了这一天:1969年3月31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上海彭浦火车站人云如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巨幅语录铺天盖地。当西去的列车长笛一鸣,车轮缓缓启动时,车站上一边是锣鼓声山响、欢呼声震耳欲聋,一边是送行人群队伍和车厢内近800名上海黄浦区知青的哭叫声惊天动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奇怪的是,站在车厢内的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张长平居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笑容满面,还潇洒自如地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和同学挥舞双手,真有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壮烈气概。说真的,我那时的心情反而充满了挣脱家庭蕃篱的快意,毫无亲情的苦涩和长期的郁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如同满天乌云,被驱散得干干净净,清清朗朗。我那时还真的有点踌蹰满志,意气风发,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次乘坐这么长时间的免费火车,第一次全程享受免费的列车盒饭,第一次见到列车上挤满了这么多胸佩毛主席徽章的“红小兵”,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新鲜。
火车风驰电掣地越过了浙江、江西地带,进入湖南后,特别是进入贵州后,便显得颟顸笨拙而缓慢,一路上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盘旋曲折的山路和数不清的隧道涵洞,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贵州瑰丽而奇异的大自然风采。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终于在4月3日缓缓地驶进了安顺火车站。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驿站――知青生涯。
二、到紫云县的第一天
390多个知青(还有近400名知青先在贵定下车,他们的插队地点是修文县)在南华饭店(已拆除)度过三宵。第四天,4月7日一早便分别登上编号的客车,向紫云进发。60多辆的知青专车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浩大车队,令观者为之驻足瞩目。
车队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安紫公路上,扬起层层灰土,路两边远处群山起伏,郁郁葱葱,山脚处,半山腰间散布着稀稀落落的农舍,大都是简陋的茅草房、石板房,极少见到一两间象样的瓦房。村寨中,炊烟袅袅,狺狺狗吠,不少老叟、村姑、小孩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车队,瞪着惊诧的眼睛,痴痴的呆立着,忘记了驱赶身边的牛羊。
车队过了鸡场就进入了紫云县境内的黄土公社,便开始有第一批知青下车,之后沿途到狗场、猫营、青海、紫松、白云,一直到望谟方向的新民、小牛场、水塘、巴寨、宗地,陆续把所有知青送到公社所在地。
我是在紫云县城下车的,因为那王生产队就在离县城四公里处的紫云洞坡背后。我永远忘不了到紫云那一天的情景,整个小山城沸腾了,全城居民和附近村民纷纷涌挤在路两边,可谓人头攒动、人山人海,象观看天外来客一样,簇拥着我们上海知青;到处是红旗飘飘,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乐曲;一拨又一拨的苗家布依族儿女,唱着粗犷奔放的山歌,弹奏着热烈、欢快的唢呐、芦笙,并沿路捧上一杯又一杯的农家土酒,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寨。
和我一道插队在那王生产队的还有两个比我小3岁的68届初中生,其中一个叫朱瑞龙,和我在上海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个叫陈福祥。我穿着卡其布学生装,他们两个身着不带领徽的军装,还带着军帽,站在一大群身穿青布民族服饰的村民而前,真可谓是鹤立鸡群、飒爽英姿了。
生产队的谢队长(一个目不识丁的苗族老农)把我们三人安顿在一个显然是仓库一样的旧草房里。我一看,房顶两头呈三角形,完全是敞空的,用竹子编织起来的房顶隔层堆着包谷。草房又分成两间,小的一间供作卧室用,另一间放着水缸、三脚架、顶罐、铁锅、砧板、菜刀、柴木之类,显然是“厨房间”。它本来应单独隔开,以使中间一间作“堂屋”,但可能一时来不及分隔,以致于除卧室外,整个草房显得空空荡荡。
住在隔壁的是一对汉族年轻夫妇:周明光和龙昌珍,他们热情主动地帮我们铺床,挂蚊帐。要不是他们帮助,我们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在床架上铺上木板、棕垫和被单,也不知道怎样挂蚊帐,在敷着牛屎的墙壁(用竹片编制)上糊上报纸……
正在发愁怎么做晚饭时,生产队的谢队长、王副队长、张会计和住在我们对面的陈大队长提来了大米、一大罐猪油、鸡蛋和盐巴,来帮我们支起三脚架、发火煮饭。一会儿,我们就吃上了一顿真正地道的农家饭: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腌熏的腊肉,盐巴辣子水沾的白菜豆腐,一锅当菜吃的面条,还有农民自家酿制的土酒。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初次见面的拘谨,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土酒在进村的路上已喝过三碗,开始并不觉得辣烈,现在发觉酒兴已发作了起来,一阵阵的热流在往上涌,不禁头晕目眩,飘飘然而支撑不住了。
我们醉倒在各自的床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醒了过来,眼前是一片漆黑。原来那时全村还没有通电,我们生平第一次摸出火柴点燃煤油灯照明。我们发觉脚下踩的不是水泥地、木板地,而是又冷又潮的泥巴地。就在此时,我们突然才感觉到,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收音机,没有城市的大马路和喧嚣声,没有熟识的亲人,一切显得是那么的沉寂、陌生和孤独。而对着如此艰难的环境,我们开始从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人间。此刻,我们才开始认真的思考:明天将会是什么?要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下地干活吗?谁来帮我们挑水买菜做饭?难道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我们三个人仿佛一下子跌入冰窟窿,久久相对而坐,说不出一句话来,而那白天还在喜逐颜开、豪情满怀的陈福祥竟像孩子般地呜咽了起来,说他想家、想爸妈、想上海。
以前听人说,还不相信贵州人无三分银,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今天正是应验了。正在感到孤苦无助、愁眉不展的时候,屋外面,天降大雨,而且雷电交加,极尽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淫威,真把我们吓坏了。草房顿时四处雨漏如注,屋顶隔层多年的积尘一片片地落下来,把我们刚刚挂起来的洁白蚊帐染成灰黑。天哪,这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述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们三个人可怜地畏缩、卷屈在草屋一隅,抖抖擞擞的,战战兢兢的挨过这漫漫长夜,直到第二天天亮。
这就是我们到紫云县第一天的真实情景。
三、第一次到黄果树
一唱雄鸡天下白。第二天一早,随着谢队长一声吆喝“出工喽”,满寨震动,大家纷纷扛着锄头薅刀,从破旧不堪的叉叉房走出,下地干活去了。没有谁来管我们。我们三个一商量:“走,到黄果树玩去!”我们把房门钥匙交给了隔壁的龙昌珍,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顺山路、淌小溪,30分钟后就到了县城。正好赶上去安顺的班车,2个半小时就到了安顺客车站,又立即搭上去镇宁黄果树的客车,中午就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世界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四月的大瀑布据说水流并不特别宏伟,但那一天的情景却使我们终身难忘。
只见气势恢弘的大瀑布自80多米高、100多米宽的悬崖绝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发出震天巨响,如千人击鼓,万马奔腾,声似雷鸣,远震数里之外,使我们惊心动魄。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描述其“水由溪上石,如烟雾腾空,势其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具不足拟其壮也”。隐在大瀑布半山腰上的水帘洞,又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天我们运气特好,观赏到了雪白的瀑流飞泻在碧绿的深潭和蓝天衬托下五彩缤纷的七色彩虹。瀑布激起的水珠,飞溅100多米高,如云漫雾绕,洒落在上面的黄果树街市。有人说,即使是晴天,也要撑伞而行,故有“银雨洒金街”之说。我们从氤氲雄奇的黄果树山水中充分地领略到了贵州安顺原生态的文化品位、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动人场面。
从黄果树返回安顺,已夕阳西下,天色渐暗了。我们三个每人花了三毛钱在西街“赵一曼旅社”住了一晚上,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返回紫云。
有必要提一笔的是,第二天正值安运司两派“革命群众”正在内讧、搞武斗,班车停开。于是,我们三人顺着安紫公路徒步前进。中午走到狗场,在一个知青点混了一顿中午饭,又继续往前赶,晚上走到猫云,只感到筋疲力尽,浑身散架,再也走不动了。于是在猫云街上的一个小旅社住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趁店员还在梦酣之中,非但没有付住宿费,还顺手牵羊,偷了一个很精致的木工小推刨,拔腿就跑了。这事虽然是朱瑞龙干的,但作为年长三岁的我,至今想起来还深深自责。作为知青,我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伤害,本身已很可怜了,但我们在那个年代里,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干了伤害比我们更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的诸多荒唐可笑的傻事。这也许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畸型特征吧。
四、插队落户众生相
朴实、敦厚的少数民族农民是可爱可亲的,要不了几天,我们很快就跟全寨人混熟了。我们入乡随俗,有时也穿着对襟上衣,头上裹了一圈土布帕,还真像电影《阿诗玛》中的阿牛那样,显得分外英武、彪悍,逗得那些苗族、布依族少女经常在我们面前故作忸怩之态,卖弄风情,有些更大胆的还让我们猜谜语:“u2018一个老者不大高,白天坠嗑睡,晚上搞夜宵u2019,小沙,你说是哪样?”当我们还在茫然不知为何物时,人群中的一个小孩就脱口而说:“那是小鸡鸡”!“哄”的一声,那些少数民族姑娘就心满意足地迅速地逃离现场了。把我们三个情窦初开的处男少年弄得脸红耳赤。
我们知青也会恶作剧。
(一)劳动偷懒,威胁记分员加工分
我们三人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从来没干过农活,这是生产队知道并且很体谅的。队里通知我们:每天只需两个人上坡出工,留一人在家挑水做饭,便算三个人每天每人都记满工10分。但我们三人还是怎么也吃不了苦。遇到下田栽秧,一个蚂蟥爬到脚肚子上,便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躲在荫凉处再也不下田了;遇到上坡薅包谷,烈日炎炎,汗流浃背,支持不住,便借口解手溜回家里,从此老将不会面。等到我们得知其中两人每天只有5分工的时候,便操着家伙上门到记分员家,威胁记分员硬要给我们补10分工,扬言如不补足工分,我们就要烧他的房子。这一贴药果然灵效,因为农民最怕火烧房。这件事我们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荒唐内疚。
(二)趁人不觉,经常偷宰农民鸡鸭
全寨人上坡下田干活去了,整个村寨内顿时一片空寂,也正是我们三人拭目以待、大展身手的最佳时机。
那王寨农民喂养的鸡鸭,是地道正宗的当地土鸡土鸭,也正是我们经常瞄准不舍的果腹佳肴。对村干部家的鸡鸭我们很少染指,只捡敞养在宅外的鸡鸭,偷来杀吃,其速度之快,手脚之麻利,自己也想不出什么时候竟学会了这一手。每当我们把鸡鸭开膛洗净、饱餐一顿后,总把毛呀骨头呀埋在山脚架的灰堆内,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了。时间一久,农民们便开始怀疑起是我们知青干的好事。有一天,也活该事情露馅。我和朱瑞龙上坡栽包谷去了,陈福祥独自一人在家,外出侦察,错误判断对门谢队长家无人,便仓惶中从他家鸡笼中逮出一个肥肥胖胖的大母鸡来,在宰杀过程中,大母鸡哀叫了几声,便惊动了队长家的小儿子,从房缝中窥见了陈福祥杀鸡、退毛、藏毛的全过程。正当我和朱瑞龙正一路引吭高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回”时,谢队长一脚跌进门来,从灰堆中刨出鸡毛,大吼一声:“你们做的好事,吃的好香啊!”我们顿时大惊失声,知道东窗事发了。但是农民毕竟是憨厚老实好哄的。晚上我们三个拿了点上海糖果、糕点上门去赔罪道歉,几句好话一说,谢队长一家也就喜逐颜开,再也不讲要我们赔的事了。只是神情虔诚地问了我一句:“小沙,上海是哪个国家啊?”村寨的村民、干部的敦厚、宽容、可爱,文化落后到如此愚昧无知的程度,一至于此,令我们至今想起来为之扼腕,可叹可悲。
(三)撒谎要结婚打家具,提刀扬言砍树林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们也象所有村民一样,分得一片树林,但当时我们三人谁也没在意,也根本没有去树林修枝培土施肥料理。待当我第一个被抽调上来、离开生产队当小学教师后,突然心血来潮,要打几样家具,便想到了我们在寨子中还有一片小树林。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从水塘小学乘车赶到那王寨,二话未说,拿起一把斧头就要往树林中跑,队里的张会计大为不解,问我拿斧头去做什么。我便撒谎自己快要结婚了,要砍自己的树林去打几样家具。张会计说:“树林是分给你们三人的,你应有一份,这不假,但现在树木还未长大,砍了没用,不如在仓库里选几块现成的木板。”我转念一想,也对,于是跟着张会计来到仓库,不容分说,跳上仓库的梁上,把大块大块的楼板(泡桐木)拆下来,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气拆了12块。顿时屋架晃动了起来。张会计急喊:“小沙,你当真要拆房子?!房子要垮了!”我只才心安理得地跳了下来。最后还是生产队喊了一个小农民把这些木板捆好,抬送到紫云县城。这12块泡桐板后来我把它们换成了一个大衣柜和一个书柜。往事悠悠,青春躁动,真是无知无理荒唐啊。
(四)鞭打倔牛出洋相
吆牛犁田,是寨子青壮劳力的活路。我们三个正值青春年华,自然不甘落伍,便主动要求牵牛犁田。说实话,那时是图个新鲜好奇。我俨然耕田老把式一样装束,头带草帽,手执牛鞭,高高卷起裤腿,赤脚牵牛下田了,但怎么也驾驭不了不听使唤的倔牛。牛不是昂首纹丝不动,便是擅自扬长而去,我站在泥泞的水田里,不禁无名火起,顿时挥舞鞭子,重重打在牛屁股上。牛被激怒了,于是,拖着我一路快步前跑。我一手舞动牛鞭,一手操持梨耙,一时按捺不住,脚底一滑,便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当我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时,周围是一片哄笑声,原来我满嘴满脸满身都是泥,活脱是一个贻笑大方的泥坯子,只是两只眼珠子还在滑稽地转。我不由的勃然大怒,找着牛鞭,寻思着给那头令我出丑的牲畜一顿狂抽,殊不知,那头牛早就踱上水田路边,正悠闲自得地吃着绿油油的青草了。
(五)骑着高头大马逛商店
在上海,我们根本没有看见过什么马呀,什么驴呀,只是在电影中看见过中国红军、苏联士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军刀、英勇杀敌的雄姿。我们也曾想象如果有一匹象关云长那样的赤兔马和项羽那样的乌骓马,那该多威风啊。现在好了,生产队有几十匹马,犹以王副队长和张会计的两匹全身雪白的马显得格外的雄壮俊健。朱瑞龙、陈福祥两人软磨硬泡,使出浑身解数,说动了两位农民,答应让他们骑一会过过瘾,殊不知他们一骑上马,一拍马屁股,马便一路狂奔,转眼就到了县城。幸好城边的居民帮他们勒住了马。于是,他们就趾高气扬地骑着马逛进了紫云县百货公司和大饭店。这使紫云县的居民为之膛目结舌,惊奇不已。这是紫云人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奇遇。而后,他们两个就快马加鞭,往青海公社海子生产队(那儿有4个女知青)方向去眩耀骑马身段了。那王生产队上海知青骑马逛商店,至今还给当地留下一段史无前例的佳话和笑谈。
五、知青生涯的反思
我在紫云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涯是短暂的,从1969年3月到1971年8月,前后不到两年。但这段终身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这里,看不到上海大都市那样宽敞整洁的大马路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看不到鳞次栉比、豪华气派的高大楼群,见到的只是一些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稀稀落落、破旧不堪的茅草房。看不到自己熟识的亲友,见到的只是一张张陌生、神情几近麻木的面孔。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音乐,一切显得那样的沉寂而单调。我们每天必须扛起锄头薅刀种庄嫁,自己挑水砍柴支起三脚架煮饭。那时汗珠子不值钱,一天辛苦劳作只不过一毛七分钱。从繁华似锦的大都市一下子跌落在一个荒凉原始落后贫困的山村,我们每个知青的内心寂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正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熟起来了。
第一,我们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挑水、煮饭、种庄稼,学会了不依赖别人而独立谋身。第二,我们较早地学会了思考。两年的知青生活,每天的辛苦劳作意味着什么,皮肉最懂得。以前是从书本上去认识,现在不得不用皮肉的体验去认识。第三,真切地体验到了沿海和发达城市同祖国内地、边陲乡镇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城市知青的大迁徙最初拉动了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们各自都得到了深刻的启迪和教训。第四,坚定了奋斗信念。“文革”使我们这代人整整耽搁了十年,更加萌发了我们这代人珍惜时间、努力拼博的信心。知青生涯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耽搁了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豆寇年华,把我们推向了生活的最低层,但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知青生涯如同共和国艰难历程一样,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奋发自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思想培养基。
当年下乡在紫云县的390多名知青,现在大部分返回了上海,留在紫云、安顺、贵阳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时或聚会在一起,我们不认为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都是悲剧,但它确实是一部难忘的、刻骨心扉的历史,它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始端,成为我们的人生底蕴。我对这段知青生涯怀有深深的眷恋。
五十载情系光明 今朝日畅述心怀
――上海市光明中学68届高中(3)班纪念进校50周年聚会侧记
时光荏冉,岁月如歌,原高一(3)班同学1962年进光明中学至今不知不觉已有50个春秋了。在班长何慧瑛代表所有同学心愿的倡议下,她与马坤蓉、郑辛逸、严钧民、王才航、单浩义等同学积极策划,组织筹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同学聚会。
2012年5月3日下午1点半, “五十载情系光明 今朝日畅叙心怀”的主题班会,在申城母亲河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滨江厅举行。
门厅前布置了一幅精心制作的海报。画面上绿色的操场铺底,百年红色校楼矗立,“光明中学”四个大字金光熠熠;湛蓝的天空衬托着这次聚会的主题,又用大红色封顶,寓意生气盎然,岁月不改心中永远光明。同学们依次在上面签名留念,同窗情谊依旧。
令大家欣喜的是有40人围成圆桌济济一堂,是毕业后班级历次聚会人数之最。除已故的6名同学和3名没有联系上的男生及1名请假之外,悉数到场。17名女生无一人缺席。定居加拿大、日本的鲍逸敬、吴丽莎同学也赶来参加。有些同学竟是1969年分赴各地后第一次重逢,握手之际,感慨万千。
“学友50年,友情长依旧。相聚虽偶尔,却惦念心田;问候虽随意,却倍感亲切;祝福虽平淡,却最见真诚。让光明照亮我们,平安、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班长何慧瑛饱含深情的致词拉开了这次聚会的序幕。
聚会有三项活动内容。首先由中心工作人员带领,参观欧洲厅、明珠厅、上海厅,尔后登上屋顶花园。浦江两岸的百年万国建筑群和改革开放以来如同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交相辉映、美轮美奂,形成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一道最具魅力、最具特色的风景线,令我们这批老三届学友抚今追昔、赞叹不已。
不吸烟、不饮酒,喝咖啡、茶水,随意品尝精致可口的中西点心和新鲜瓜果,也算是享受了一顿绿色健康的下午茶,席间自由交谈,其乐融融。这是活动的第二项内容。
接下来就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敞开心扉,情系光明,畅叙衷曲。饶有兴味的是,安排发言的次序是按照当年班级同学的学号依次进行。笔者实在不能一一录下每位同学的精彩发言,只能择其要点,概括一下这次聚会畅叙心怀的特点。
特点之一:真诚坦率、感悟人生。同学们打开话匣子,纷纷回忆光明的生活,感恩光明中学给予的良好的学识和品行教育,并从各自一段段插队落户、参军、从教、务工、从政的生活历练,折射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共和国成长历程息息相关、紧紧相联。这段经历,是一部难忘的历史,成为我们思想的培养基,它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始端,从而成为我们人生的底蕴和财富。
特点之二:心态良好、积极向上。我们这班同学无一例外,都已步入耳顺之年,退休在家了。在大家的发言中,可以听出虽都晚霞夕照,却绝不怨天忧人、自甘寂寞。或坚持锻炼、养身修性,或亲操家政、呵护儿孙,或练字操琴、吟诗作文……。还有一些同学至今在发挥余热,如郑辛逸同学受聘续修上海政府志,沙岚同学参与组建社区文化室,王才航、张锦江同学受聘于机关、 企业,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为年轻人传经送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特点之三:书生本色,妙语如珠。在同学们的发言中,仍可以窥见他们当年学生时代的意气风格。吴国光同学慷慨陈词,滔滔不绝,纵横捭阖;虞顺航同学发言充满诗情,反映出他是俄罗斯文学、莎翁戏剧的粉丝;严钧民同学的深邃,余绍钢同学的沉稳,盛继抗同学的精干,封黎明同学的温婉,华佳芳同学的质朴,单浩义同学的勤勉,吴丽莎同学如男生般的刚健……。
座谈会中,不时欢声笑语四起,互道平安健康珍重。最后,马坤蓉、张锦江同学组织大家摄下了这次50周年聚会的一张张弥足珍贵的镜头。
谨以鲍逸敬同学的当日诗作《同窗五十周年记》作为本文的结束:
“坎坷岁月一代人,磋砣人生不沉沦。
慷慨惊叹当年狂,光明学子真情深”。
沙岚书法
沙岚老师从小酷爱书法艺术,楷从颜、欧入手,行草先以两王、唐寅、文征明的书贴为范本,后自成一体,书写流畅、灵动。沙老师现为贵州省安顺书法家协会会员,近年定居上海金山,并加入金山区书法家协会,积极从事书法创作活动。
沙岚藏石
沙老师是一位玉石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奇异趣石精彩无比,玉、石难辩,件件是宝。
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