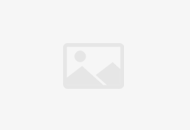谭国玉的个人简介
谭国玉,山东文登铺集镇东谭家口村人,生于哈尔滨,1949年07月参军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保送入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学习。毕业后留学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获副博士学位。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简介
谭国玉(1930.3-2009年8月2日),男,1949年7月参军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保送入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学习。毕业后留学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获副博士学位。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谭国玉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土壤切削试验室的建设与土切理论研究及应用指导,撰写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土切理论方面的论文,并获国际优秀论文一等奖;参加了74式全液压挖掘机、推土机、拖式布雷车总体方案的咨询、论证、设计、试制、试验与鉴定等方面的工作,该项目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三等奖;参与研制的八四式重型机械化桥,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__吴新明
早就听说过谭国玉将军的大名,他雇农出身,七岁就给东北抗日联军地下党送信,十七岁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的指导员。1953年仅有初一文化的谭国玉阴差阳错来到了军事技术的最高学府――哈军工。面对着科学文化的堡垒,谭国玉屡次碰壁,但在陈赓的亲自关怀下,谭国玉奇迹般地克服了自卑,战胜了自我,由门门不及格到毕业时成为学院的全优生,在哈军工早已被大家熟知,但个中成长过程的酸甜苦辣却鲜为人知。
2008年10月16日上午,新街口第二炮兵招待所会议室里热闹非凡,
许多白发长者(基本上是80岁左右的老人)满面春风地来到这里,他们相互间握手、拥抱!好多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今天召开的是哈军工一期学员入学55周年、毕业50周年座谈会。55年前,这些热血青年带着满身的征尘和硝烟来到哈军工,立志改变我军的装备技术面貌,55年后的今天,功成名就的同学们在一起回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心潮怎能不澎湃?!经校友介绍我们找到了谭国玉学长,表示了采访意图,告诉他为了纪念母校,我们准备拍摄一部大型系列片《哈军工》,听后,他有些不太愿意,但经不住许多老同学的劝说,有一位女同学甚至说,为母校做贡献你拿什么架子?只要同意你接受采访我就拥抱你一下,说完真的扑了上去,大家哄堂大笑!在一片笑声了,采访开始了。
上错车误入高等学府--哈军工
谭国玉告诉我们,他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1930年生于哈尔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从外表上看他身体结实,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透过镜片可以看到他军人的刚毅的眼神,微微下弯的嘴巴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他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大方,人缘关系极好。谭国玉讲他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贫雇农,靠给地主老财当长工糊口,在山东混不下去了,父亲便延着祖辈传下来的老路,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当了铁路工人,尽管苦难无尽,颇有见识的父亲说什么也要让自己读书。
谭国玉自小就对旧社会的不平恨之入骨,一边读书,一边给当地下党当上了小交通员。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由于作战勇敢,没多久当就上了班长。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东北随着四野大军一直打到广东,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的指导员,这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成长为解放军的模范基层干部。
谭国玉告诉我们,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初,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工作,当时我任指导员,负责扫盲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更需要提高文化修养。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战争期间我们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记得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时在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大批的汽车由于没人会修,没人会开,又不能留给敌人,只好都炸了,实在可惜!如果把那些东西弄回来装备部队有多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一定要学点本事,那时候,我才18岁。到了1952年,这个求学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部队扫盲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就向上级部门坚决要求进速成中学学习,我们团的政委马书群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把这一期扫盲工作搞完了,我送你到速成中学!”后来他把这事忘了,但我可没有忘记,扫盲工作结束之后,我不依不饶地找马政委说,首长你说话算不算数,我这一期扫盲工作搞完了,你该送我到速成中学学习了吧。
他嗯呀一声说会兑现承诺的。我半信半疑。几天后,部队突然通知我,说想学文化的同志集合,我心里很是高兴,看来我进速成中学的愿望实现了,立即打好了背包。然后,我上汽车,再上火车,一直被拉到哈尔滨,一下车我就问,这个就是速成中学吗?请把我送到送到预科安排吧。来接我们的同志大笑,说你这个小傻子,这个是大学,军队的高等学府。
我做梦也没想到,只敢进速成中学学习的我竟然来到了大学。
我吓坏了!
我简直在怀疑自己是被人拐进大学里来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直觉告诉我,我得赶紧走,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来接我们的高勇指导员说,你不能走,来这还得复习中学的课程。我问,我复习什么呀?他说要复习高中课程。我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还复习高中?赶紧放我回去,我还是回去当我的指导员去。
他说不能走,得请示请示请示。
他连说了三个请示,他具体请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被留了下来。
学院让我先进预科,补习高中课程,补好了再学大学课程。
课本发下来了,都是高中的数理化,我翻翻,什么都看不懂。数学课,只学过小学的四则运算;化学课,只认识一个表示水的符号;物理课是“鸭子听雷,石头落井”。这时的我面临一个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处处是难点的严峻局面。头两个月的测验,门门功课不及格。到了四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5门功课按5分制计算,一共得了7分。我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后典型,一时间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吃不下饭,苏联顾问打算让他回原部队。
我感到自己底子实在太差,根本不是上大学的那块料。这样下去,迟早得被学院除名,倒不如自己主动提出回原部队,还可给学院减少一点麻烦。他于是向区队长递交了一份退学报告。我对同学们也放风说,要重回那个“老虎连”当指导员去。
陈赓院长留住了我
要通过入学考试了,那时候学院实行的苏联的5分制。但我们的数理化入学考试,实行百分制,三门课我一共得了7分。这时我又悲又喜,悲的是我水平太差了,喜的是这回可有理由回部队了,我门门不及格你们总该放我走了吧。但学员队高勇指导员说不行,你不能走,你还没有毕业,你先试着跟一段时间看一看。我无奈极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也只好照指导员讲的那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但心里真的没底,同学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有的还上过大学一二年级,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学了那么点东西,又逢战争年代,都给忘光了,说实话,当时我连数学的四则运算题都不会,那水是H2O的分子式我也不懂,化学基本上全都忘了。
怎么办?我只好拼了。同学们学八个小时,我就学个十二小时。拼了一个月,分数始终是零蛋、2分,零蛋,2分。我好心酸啊,又提出了要走。这高等学府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坚决要走。我对高指导员说,大家学8个小时,我学10个钟头,20个钟头,我抱着人在阵地在,命都可以不要,但还是不行,学习这玩意不是打仗,这是攻克文化阵地,是需要底子的,这个不是好玩的。
高指导员也很无奈。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情况让陈赓院长知道了。有一天,在早操后休息时,陈赓院长见到我,就让身旁的秘书叫我过去说话。
陈院长笑着说:“你是谭国玉吗?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要走?”
我垂着头,说:“是!”
“我听说,你扬言人在阵地在,一定读好书,他娘的,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党和国家准备了这么好的条件培养你们,你不好好学习,还整天想着脚底板抹油!”
我说:“这个地方不是我呆的,院长,这个地方是高等学府,我周围同学不是上大学一两年,两三年,就是高中毕业的,只有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怎么可以弄在一起?再说,我进来不是正规考的,是混进来的,我要上速成中学!”
“那也不行!你必须给我好好学,我告诉你,你必须好好学习,你要实现人在阵地在的诺言!”
然后,陈赓院长走了,中午休息时,他又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我原先不知道他住在哪,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他宿舍,一间不到20平米简简单单的小平房,他家的一小桌子上摆好了饭菜,陈院长叫我吃饭,我知道院长待人亲切,也就不客气了。院长一边吃饭,一边笑哈哈地骂我,说我不争气。我心里说,这哪跟哪呀,争气也不管用。我是铁了心要走,就跟院长顶起牛来了。我说你院长是叫我吃饭还是要骂我,我是真的跟不上,我已经下功夫了。
院长说真跟不上?你下功夫了?
我还告诉说,别人用8个钟头学习,我用10、20个钟头,我们学员五队周围凡有亮灯的地方我都去过夜读,他们不让我在那里读书,熄灯之后都把我往宿舍拽,我没办法买一堆手电筒,夜里拿手电筒照着在被窝里面读书,就这个样子,我考试还是没及格,院长你还放了我吧,求求你了!
陈赓院长瞪着个眼说不行,哪有一个革命战士讲人在阵地在,结果你啥也不是。最后院长说:“好吧,不管吃饱没吃饱就这样,你不准走!”
陈赓大将忙嘛,笑着下逐客令,我抬腿就走了。
在陈赓大将特别关爱下成长
院长留我,没辙了,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苦读。
这个学习真的非同平常,白天上大课,下课吃小灶。我前面说的那几位教授,包括曾石虞等教授都在我身上下了大力气,付出了相当代价,辅导完了,还找学习好的同学帮助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数学偶尔能得3分。开始我自己也不相信,去问老师,我连初中还没有复习完,高中才开始,水平很低,这3分是不是您照顾的,怕我学习落后影响班的集体荣誉。他们说不是,只是说明你这个概念懂了。
我知道老师们是在鼓励我,所以,我继续硬拼。后来的考试,我还是在2分、3分、2分之间兜兜转转。很快就接近预科入学考试了,那是7月份,考试之前,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考也不及格,考之前我真的不想干了,想脚底板抹油溜回部队算了。
我的老部队是东北野战军独立17师211团,我是二营四连指导员,我们部队跟着林彪的总部走的。团长刘德瑞要我回去,还给我来信,说小谭,不行回来吧。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在部队还是好样的,没有丢过脸,可我在文化堡垒面前丢尽了脸面,我是说什么也要走人!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情况又让陈赓院长知道了。他叫我去他那里一趟,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啊!
那时候每一分钟,每一秒对我来说比黄金还重要。我的家就在哈尔滨,老父亲、老母亲都健在,兄弟姐妹都在,出去这些年没有回去过,为了保密,写一封信都通过武汉的部队营房来中转,因为我们这支部队一直打到海南,我们从深圳返回,最后来到武汉,所以我的家信都是通过武汉那边由我爱人给转到哈尔滨。那一两年,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回家,也没有机会考虑回家。现在,我要回老部队了,这可是比回家还重要啊,这时候谁要占用我的时间,我是不答应的。陈院长叫我去,我去干什么?我不去,我一分钟都比黄金还金贵,不去!最后,陈院长专门叫通讯员专门来找我,我无奈只好去了!
陈院长问:怎么?想通了没有?
我说没有。
还要回去?
我说,还是要回去!
“你想通也好,想不通也好,你死也得死在哈尔滨这个地方,你就别想了!”陈院长斩钉截铁地说,看我脸色不对,口气又缓和下来,“你好好学吧,但你要注意学习方法,有学习好的同学,你要观察他们是怎么学习的,你光自己闷头学不行,人家一个钟头就比得上你十个钟头,这学科学得有方法!”
一语点醒梦中人,这一下子,我算是开窍了!
我说:“好,按照首长指示办,学习人家的先进方法!”
“那就滚吧――”陈院长是幽默大师,乐呵呵地对我说。
我也乐了,抓抓头皮,一溜烟跑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比吃了蜜糖还舒服,还轻松,因为我明白了,我以前学习下的是笨功夫,面对强敌,只是一味强攻,没考虑过智取。
我开始学习同志们的好的学习方法,比如每堂课之后,我都及时做小结,一个单元结束了我再做单元小结,不管怎么样,从概念开始一丝不苟按照大纲学习,就这样苦读硬拼加巧学。
据他的同学们回忆,当时谭国玉真的拿出“人在阵地在”的精神去攻克文化堡垒。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决心在短短的5个月内系统补完初中、高中的数理化。他恨不能一天24小时统统用于学习,侵占他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就好像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他把什么时间都用上了,还是不够用,只好侵占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不仅中午不休息,夜间也常整宿的“开夜车”,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晚上熄灯以后,常常一个人溜出学员宿舍,专找有亮的地方学习。班上每周都要发生一两次“谭国玉不见了”的“失踪事件”。班干部深更半夜四处寻找,从地下室里或者拐弯抹角的楼道里,把他押回来睡觉。有几次竟发现他晕倒在锅炉房里,大家赶快把他抢救。医生说他用脑过度,太疲劳了,必须恢复正常休息才行。可是谭国玉在门诊部休息几个小时,又弹簧似地跳起来,匆匆赶回教室,他可不敢耽误一点点课。
为什么要这样做?谭国玉说,是因为自己真的很想学习,因为以往在战场上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我心里很清楚只有读好书,才能在新中国大有作为。想打退堂鼓实是因为我底子太差,太没信心,现在既受了陈赓的亲自启蒙,感到有可能学好了,所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反正是人在阵地在,我拼了,多次累倒多次送进医院,我又多次从医院溜出来。
那个时候年轻,脑子就是好使,现在我都感觉奇怪,怎么那时记忆力那么好,每个规律、定律都记得牢牢的,物理老师推导的公式由头至尾,数学老师推的拉格朗日方程等等,我都记住了。但是,就算是这样拼命,我在入学本科考试时,还是有两门不及格。按学院的规矩,一门不及格就回预科学习,两门不及格就退学,我难过死了又高兴死了。难过死了是因为我知道这次真的丧失了学习机会,高兴死了是因为再也不用过这苦日子了。
没想到,这时候学院刘居英副院长又拉了我一把。那时,苏联专家那么压他,甚至当着我的面都说过,你们把这样的人弄来学习,有辱高等学府,他谭国玉顶多能回预科去学习。那时,苏联人是很有权威的,但刘院长顶住了压力。
今天,我想起这些往事,都无感激他们,也无限感慨除了老领导陈赓大将,刘居英院长对党的事业是那么的忠心耿耿,他们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我也知道,他们跟我没有私情,也不是一定要特别地对我好,而是因为他们对具体工作有着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就是他们面对的一件具体的难题,所以,他们要改变我,最后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不是读书这块料,他们硬是将我培养成这样一块料。
在刘副院长的关爱下,我由预科进本科,当试读生,说好了,试读再不及格就走人。
这时候,我精神就轻松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们领导了,确实,我那时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只盼望对得起我的领导和老师,反正,我承认自己不是读书这块料,我就要走了。但是院首长陈赓大将,刘副院长,还有唐凯系主任,林铁峰年级主任,那可不得了,都来找同学帮助我,老师也来给我吃小灶,我前面提到的老师们在我身上下足了功夫,每个公式,每个概念我弄清楚了,他们才放心。
我第一学期就是这样学的,一边学大学课程,一边学高中课程,还一边补习初中课程。我得抢时间,为此,我有时也挨批评――说不遵守作息时间,我怎么能遵守?批评就批评,你批评我不纠正,继续学习。后来,很多同学给我介绍先进的学习方法,我十分重视。在老同学谢光(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杨桓(第二炮兵副司令 中将)、郭群芳等人都曾帮助过我,这种同学的感情,友谊是很难说的,表达不出来,很深。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入了本科当了试读生,第一学期结束,都及格了,但正式考又考坏了――有一门不及格,就是化学。平常测验都及格,到正式考时却不及格了。另外两门则及格了。按规定,有一门不及格就要退回预科,但学院不叫我回去,叫我继续学习,本学年年底,我化学也及格了。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敢松口气,因为有个叫克拉西霍夫的苏联顾问一直盯着我。
敢与苏联专家叫板
工程兵系苏联顾问克拉西霍夫怀疑我的成绩是假的,是那些教授照顾我的。年底考试时,别的同学考试他不进教室监考,轮到我进考场他就来了,好象特别优待我!人家抽一个卡片就可以了,他得用两个三个卡片考我。前两次我没有犯浑,还说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就受不了啦,说你这么优待我不对劲啊。后来,我还向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样做明明是刁难人嘛!这让我们系主任唐凯都为难了。我反过来还得安慰领导,我说主任请回去吧,物理这门课我不拿5分不姓谭,这回非让苏联专家看看我马王爷有几只眼!
说实话,这时我读书的绩效可谓突飞猛进,所以自信心十足!
结果,考试果然得了5分。
因为那个大纲是固定的,是有限的,依照大纲考试我完全有信心。
没曾想,苏联专家也犯浑了,一直盯住我不放,甚至,最后到毕业考试,还不依不饶地盯住我。毕业考试很重要。这回,苏联专家还来了两个一道考我,因为他们听说我谭国玉得了5分了,不相信,就亲自来考察。嘿,我抽了一个卡片,开始答卷。这回,我们主考老师都生苏联人的气了,他也不跟苏联专家商量,就是给了我5分。苏联专家无话可说,但还是不信我的水平,又让我再抽一个卡片回答,我在黑板上答,主考还是给了5分,完了,苏联专家又让我再抽一个,我虽然有点不耐烦,但还是答了,结果还是5分。
这次考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听唐凯系主任说,这回,苏联专家服气了,后来又听刘副院长对苏联专家说:
“你们这回总该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打胜仗的吧!”
我就这个样子,总算连滚带爬,把几个学期爬过来了,爬完了以后,该毕业了,上级领导又打算叫我去苏联留学,这又吓了我一跳,我说我不适宜,应当请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去。正好工程兵几位部长来要人,就把我要到工程兵总部,不巧那年黄河发大水,郑州铁路桥被冲断了,周总理命令陈士渠司令必须保障南北通途,一定要把浮桥架上去!
这不就叫机遇吗?那时工兵还没有技术单位、科研单位,新成立一个科研会,会长唐泽明将军,下面成立几个组,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被分在野战工程机械组,上级叫我到现场当技术员,当工程机械组组长兼技术员。我到了后,发现黄河浪头很大,把舟桥打得一套一套地翻,90汽艇下去就打翻了,人员被扣到底下,人钻出来的就活着出来了,钻不出来就死了,虽然穿救生衣。
这时候,我又遇上了老冤家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他也来到现场,我内心想真是冤家路窄。他对我说,苏联的装备用到哪个国家,都通用的,为什么对你们国家不行,你必须下去给我试。我说不能试了,世界就是一条黄河,黄河的漂流物是世界上唯一的,泥沙漂流物把螺旋浆给缠死了,泥沙把发动机的滤清器给堵死了,你发动机还能不开锅?!克拉西霍夫固执得狠,他说是你们没保养好,没驾驶好。
好多同事也都认为是这样,我明知克拉西霍夫说得不对,但也没话讲,顶撞不得。后来调拨来了苏联的150汽艇,速度特快,是周总理下的命令调来的。
接下来,架桥。
150汽艇有两部发动机,150匹马力,用来顶推门桥。克拉西霍夫硬叫我驾驶这个新装备,说是通用的,我说不妥,你们通用世界各国哪都行,但世界上只有一条黄河,这泥沙漂流物不解决,汽艇必定被打翻。克拉西霍夫说不对,并命令我你必须驾驶,我性格倔强,就是不去。
结果,克拉西霍夫把我们部长唐泽明将军叫过来了。部长说:谭国玉,下,你要尊重他!我说要解决技术问题,怎么能算不尊重?
命令必须执行,我也只好救生衣一扒就下水了,汽艇发动后开出不到100公尺就打翻了,结果把我漂流到30多里的下花园才被救起来,后来发现,我的右耳磕到螺旋桨边缘上了,我的软骨也被打断了,最后穿救生衣水淋淋地回到基地。
我对部长说:不能这样,克拉西霍夫叫下就下,现在汽艇翻了,你得弄回来。我回来了,汽艇还没有捞出来。
当时,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还在指挥部,唐部长不好说什么,就当着他的面说:现在我宣布指挥部给你立三等功!
我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不值得给我立功,这纯粹是汽艇的实际使用问题,苏联专家克拉西霍夫也意识到他的指挥有误,就开始支持我。
后来,我连续搞了几项技术革新,解决漂流物的问题,用网罩,搞清悬浮物体,后来就成功解决泥沙过多堵死滤清器的问题。
克拉西霍夫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之后,领导又叫我去苏联留学,于是,我就来到苏联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当了好几年的研究生。事情真凑巧,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古比雪夫工程学院我又碰见这个克拉西霍夫的苏联专家,我们两个在一个教研室,这时他对我是早有领教,再也不刁难我了,相反处处帮助我。我在另外一个专家的指导下学习,最后顺利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然后就塔上了回国的路程。
访问到此,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为了我们的采访,谭国玉将军那天失去了一次同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我们突然悟出这大概是那天开始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原因吧。
情系哈尔滨
为了大型系列片《哈军工》的剪辑的需要,2009年5月25日我们又一次来到北京,找到谭国玉将军的家,这时将军正在301医院住院,电话里得知,他已经双目失明了,而且,基本上是卧床不起,心脏病很厉害,得知我们需要他的影像资料时,他很热情地告诉我们,补拍是不可能了,但可以到他家里去找旧资料。在他夫人的帮助下,自费给我们转录了资料,当我们表示应当由我们付款时,他很生气地说:“为了哈军工的事情,最好不要谈钱!”我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分别时我们衷心地祝他早日康复。
2009年7月,还是工作的需要,要请他帮助修改他的采访录音稿,我们又一次扣开了谭国玉将军的大门,这次刚好他在家,不过已经是坐在轮椅上了,加上双目失明。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他诙谐的说:“这次手术,上帝夺走了我最后的一缕阳光!但是我还是想回哈尔滨去看看。”他夫人接过话题说,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还去看什么?!将军说:“我去哈尔滨,可以用耳朵听,用手摸,听一听,摸一摸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我们听了鼻子都酸了,眼泪在眼里转,好在他看不见。忙安慰他,等他身体好些时候,一定陪他去!哪知道这次访问竟成了诀别!将军带着遗憾、带着对哈尔滨、哈军工的眷恋悄然地于8月2日走了。走前告诉家人,务必把他用心改的稿子在家里收藏,把系列片《哈军工》光盘也收藏好!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悲痛,我们向将军表示,您的遗愿一定会满足!归来吧,哈尔滨人民热烈欢迎自己的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