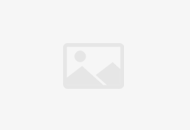孙雪峰(作家)的个人简介
孙雪峰笔名雪峰,当代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1978年2月2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曾任《当代中国》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诗人》杂志社副主编兼评论部主任。1990年开始创作,著有文艺评论作品《断――谈野人诗语言艺术特色》、《我就是世界创造自己的地方――读特兰斯特罗默的诗》、《知不道人》等,《虚笔梦花》系列诗集《我背着夜行走》、《穿越时间的思绪》、《造字》,中短篇小说《缝补岁月的人》、《时间的中心》、《拾荒者》、《凶线》、《雪橇》、《谋杀》等。
基本内容
笔名雪峰,当代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1978年2月2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曾任《当代中国》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诗人》杂志社副主编兼评论部主任。1990年开始创作,著有文艺评论作品《断――谈野人诗语言艺术特色》、《我就是世界创造自己的地方――读特兰斯特罗默的诗》、《知不道人》等,《虚笔梦花》系列诗集《我背着夜行走》、《穿越时间的思绪》、《造字》,中短篇小说《缝补岁月的人》、《时间的中心》、《拾荒者》、《凶线》、《雪橇》、《谋杀》等。
思言领悟
孙雪峰以其思与言领悟“虚极缘在”湍动之息、不言之美,对当代诗歌、小说和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发展作出探讨。
通过《断――谈野人诗语言艺术特色》、《断刃――剔开“语言隐喻”的野人诗》、《零度之外》、《另一种想象》等作品,透过对“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的发掘与张散,对野人(洪永泰)诗“虚-象”结构式的解释,阐发了野人诗语言“情真、语凝、意动、审美创新”等特征,指出其通过可思感的意象结构趋构,带人入那虚极自持而不可感的不可说之境,为当代诗歌创作开拓出崭新的意蕴化途径及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试图探寻一条汉语言创作独特的意念性统觉审美之路。
并通过《我就是世界创造自己的地方――读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死神唇边的笑――再读李金发》等作品,探索了文学作品的纯思文本的无意义缔结机制。此外,他还凭借《知不道人》、《画在人间,神思在天外》、《残缺的走失》等作品,通过对老可、黄沧粟、路中汉等当代画家的研究,探讨了艺术作品意念性构成的审美蹊径。尤为关注网络诗人、非主流诗人的创作状态。
纯思之诗
他的诗深受道学、佛学、现象学和野人诗影响,以纯“思”反构 、体验与言说相交合、视域引发式的言语方式,充分挖掘语言隐喻、隐寓与征象的特征,并激活了汉语言赋声象形、蓄势而生的天性,试图重塑语言的诗性,触及诗意地栖居。
如《拓荒牛》:
记忆割断韧角
搅着犁过的时间
在裂缝处
啃嚼遗忘的厚度
岁月沉在眸底
噙着
冷却的自尊
煮在血中的枯骨
开成荒野里
皲裂的泥土
诗中建构了一个被遗忘的开拓者、先驱者、守护者形象,他如同仁慈的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子女,却得不到理解与赡养,被遗忘、抛弃、屠戮,惟有含着泪,葆有着孤傲却已冷却的自尊,在“犁过的时间”中“啃嚼遗忘的厚度”,纵使如此,仍不惜身化泥土,执著守望!既有对现实现象的意象化构拟,又深蕴着人言说向语言言说予让,达向“存在而为自为存在”的领悟。
再如《抛弃》,追随着荷尔德林“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追问,以及海德格尔对此追问的回应。
光
被压成光影
塞进脱落的季节
扭曲
颠着迷乱的脚步
踩折了失落的坐标
贫乏
剔开挣扎
策动颠覆的阴谋
黑暗控诉着
它的枯萎
在贫乏的时代,人被物化、异化,精神被导向虚无,人们试图抛弃传统乃至颠覆一切,却又无法逃脱传统的桎梏,惟有在畸形的扭曲中挣扎乃或狂欢。促使人思索天性的回归与重构。
而在《造字》中,汉语言赋声象形、蕴势而生的天性激荡迭起,沉潜着诗人造天赋之“字”,造思言之“字”的梦想:
意念
疲倦地
分娩着语言
异化
被串成符号
晒在时间的陡坡
沉积
踩着一个
潜伏的世界
通过这些纯思之诗,表现出诗人对于开端之思的叩问,对人性回归和大我重构的呼唤,对于未来历史的思向,以及对于终极意义的寻找!
“势小说”的探索
他以“现象趋构,因形造势”为名进行的“势小说”实验,把现实引向现象,以现象昭应现实,即以世界显现之“象”达向“象”构现实的纯思文本缔结,探索当代全球化、异化背景下的汉语创作。作品以意念取势,因现象而造势,奇幻诡谲,“象”构迭生,又与严格意义上的现实息息相关,以对现象的“虚-象”结构趋势建构的诗性结构,意念性地表现纯思之美,探索存在的意义。
如《缝补岁月的人》,讲述了一个人不断地裁开、破坏属于自己的世界,又不断地缝合,直到他配了一副眼镜,想认清这个世界,可是戴上眼镜之后,却又分不清哪个世界才是他真实所在的世界。他把眼镜砸碎,再缝合之后,奇异地发现自己居然有了一双复眼,表现了不断更迭的人领悟世界的基本方式;《偷窥》、《时间的中心》等作品则直接接驳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隐寓着“人从虚无中来,经历痛苦与荒诞的存在后又消散于虚无;人都是孤立的,无法沟通,也得不到救助,外部世界也是个毫无意义的存在,人生存的周遭环境已严重物化,人为物役,丧失了主体性;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呈荒诞状态,人在不可避免地成为非人”,继而召唤人性的复苏!
《谋杀》表现了主人公不断地往返于蜗居的现实与敞开的现实之间,总觉得有人或者什么事物会在这条道路上,意图将他谋杀,因而终日惶恐不安,但是终未能逃脱被谋杀的命运,在临死前,他发现谋杀他的竟然是他自己,隐喻着人与自身、人与现实的冲突,从而引发读者思考人存在的现实意义;《拾荒者》则直指社会现实,通过一位拾荒者辛苦营造着属于自己的居所、微末的领地,却又被无缘无故强令拆走,继而被火烧死的意念性营构,表现了人作为孤独个体的“孤岛效应”。《雪橇》通过一个被诬陷为谣言的散播者,在经历逃亡之后,竟被自己求助的对象野狼撕食,在他临死前,却看见雪原上,一个人正像他一样驾着雪橇,不停地绕圈子。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寓言式异化,发觉了语言的迷雾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的隔阂,其目的仍是为了探寻存在的意义,人们发掘语言或者抛弃语言,正是为了超越语言的局限,寻找新的沟通渠道。
作为一种新锐的语言实验,还需经历思与言和时间的炮烙与考量。
思与言
1、虚持者敞开为虚持之“象”,并称命于虚持。
2、人把握世界的本基思感趋向――涌现!本原结构为维持自身,而扩张自身趋向结构、吞噬他向结构,并与此同时降生新向结构,而本原结构仅仅通过结构着结构而护持自身的“涌现”,为人领悟世界,筑基拓原。人作为世界之缘在,从生发处即与世界葆有着同一隐秘结构,在世界结构对人结构的结构中,人趋向于对自身结构的完成,人昭应世界并领命于世界的呼唤。
3、人透过感觉领悟世界,并凝向意念。
4、人即世界――“人”即世界的“虚―象”结构,“人”的思、言、为意味着“人的世界”的边界……
5、猴子从树上跳到地面,颤悠悠地站直后,再去抓捕猴子。
6、人的罪恶取决于欲望的实现,而非欲望本身。
7、作为风干而出音与形、思与美的标本,汉语言全部的奥秘,就隐藏在其蕴行的征象与隐喻的言语之间。
8、不同的意象都可以随性地引入诗之结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性关系,它们只在诗之缘构中产生关联,此种关联的妙处在于,这些毫无逻辑关系的意象,被抛投在结构中旋荡,意象任何组织、罗列、碰撞都会产生新的意象关联,并且在蕴境上,成为和现象相匹敌的“象”构。
9、由动词营构的动态意象趋构使得诗之结构犹如讳莫如深的巨大漩涡,呈现出循环不止的旋动构成趋势,生活灵动、动感十足。
10、野人诗如同语言蒸发后浓缩的结晶,总把意象凝到极致,再勃然发动,如同被拧紧的发条,在松开的刹那,不受方向与时间的约束迅猛地旋开,达向永生永动的美之自美,充沛着发散性的特质。
11、野人的“情”中,显有教化式的“以理服人”,却震烁着冲击人心的“以情动人”。野人的“情”,让作为生命第一感觉之“情”,穿透语言,并使之发光。愈是简单、凝练、纯真,乃至天真,愈涵酝着相机而发的绝大气蕴。此一情,率真而蓄,待机而发;此一情,凭空蕴势,虚极而动;此一情,突破黑霾,普照精神。有此一情,才有“古道,西风,瘦马”,才有“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才有“情感的黑洞”;有此一情,才有“大江东去”,“醉里挑灯看剑”,才有“那真实的疯狂/是否还在墙上”。